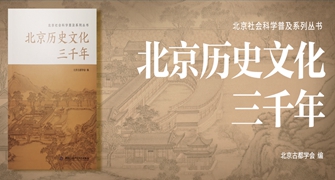清承明制,也基本沿袭了明代后期的坛庙祭祀。乾隆时期,又对北京坛庙进行大规模的修缮与完善,北京坛庙文化达到繁盛时期。比较典型的如历代帝王庙,清廷多次更改入祀帝王名单。顺治年间将明末帝朱由检、明太祖朱元璋移入,又增祀辽、金、元三代帝王。康熙六十年,圣祖重新确定,只要不是无道被杀或亡国的帝王,都可入庙享祀,入祀数量由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详情】
明代是北京坛庙变化与成型的关键时期。明初太祖以应天(今南京)为都, 其国家级坛庙皆分布于金陵城内外。攻下大都的徐达,则受命捣毁胜国之都, 代之而兴的是燕王的藩镇坛庙。“靖难之役”后,成祖决意迁都北京。永乐年间, 他一方面在北京大建皇宫,同时仿照南京形制,修筑各种礼制建筑。《明实录》有记“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 奉祀天地、日月、山川、祖先、社稷的坛庙,逐渐在北京建成。【详情】
坛庙建筑是都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中国传统礼治体系中尤其占据着核心位置。坛即祭坛,东汉《说文解字》释为“坛,祭场也”,原义是指在铲除杂草的平坦地面上,用土筑堆用于祭祀神灵的高台,所谓“筑土为坛,除地为场”。庙即宗庙,《说文解字》释为“庙,尊先祖皃(同‘貌’)也”,后人注称“古者庙以祀先祖”“尊其先祖,而以是仪皃之,故曰宗庙”。【详情】
会同元年(938 年),辽太宗耶律德光从后晋石敬塘手中获得幽州(今北京),当即升为陪都,称“南京”,又称燕京。北京由此拉开迈向统一多民族国家首都的历史序幕,也开始了北京坛庙从地方向国家层面转变的步伐。作为辽代“五京”之一,燕京建有皇城及相应礼制建筑。史书记载,辽代南京皇城内,“有景宗、圣宗御容殿二”,此可视为国家祭祀建筑的滥觞。不过辽代燕京仅为陪都,不仅兴建的坛庙数量较少,祭祀礼仪也相对简陋,其重要性远不能与辽上京临潢府(今赤峰林东镇)相比。【详情】
什么是宽容精神?实际上,在李大钊的文章中没有用过这个词,常用的是“容人”“相容”“调和”等词。后来的研究者把李大钊讲到的意思,概括为“宽容的精神”。看来,比较确切地反映李大钊这种宽容精神内涵的解释, 还是用《新旧思潮之激战》中所说的“容人并存的雅量”和“自信独守的坚操” 更为恰当。【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