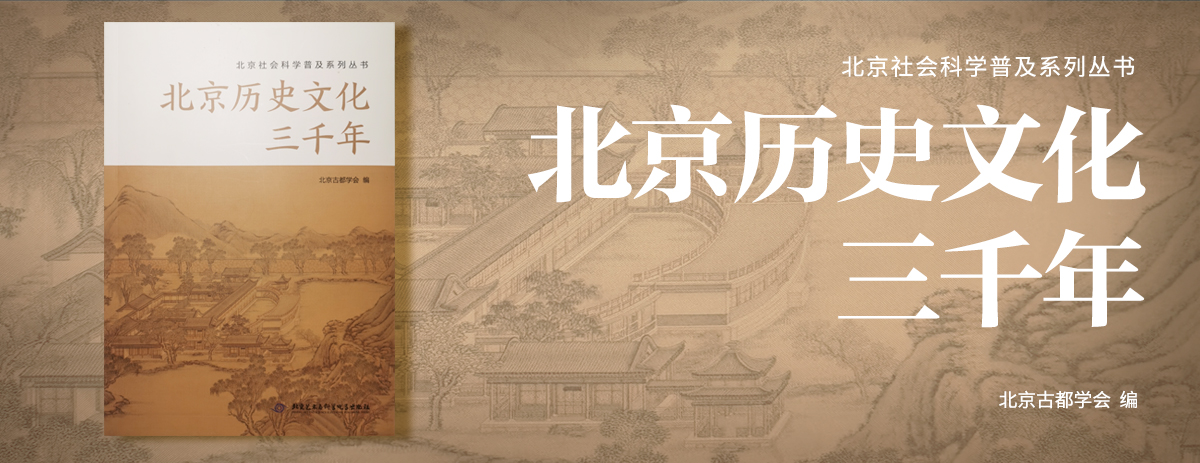来源:人文之光网 发布时间:2021-09-06
北京之所以被誉为“万古帝王之都”,除了“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的山川形胜之外,“会通漕运便利”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另一个地理因素。城市发展进程与区域文化源流显示,大运河不仅是供应国都漕粮的经济生命线,而且是北京文脉的重要地理标志。放眼全国,自江南至华北,大运河流域凝聚了底蕴深厚、风格鲜明的地域文化,最终积淀为以这条绵延三千五百多里的人工河道为象征的“运河文化带”,北京段是其中的精华地段之一。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特征决定了众水朝东的基本流向,大江大河由此成为南北交通的阻隔,开凿运河就成为从水路实现“天堑变通途”的重大措施。汉唐长安、洛阳与北宋开封等人口高度聚集的著名古都,都曾依靠运河之上输送的漕粮作为经济支撑。在天然河道未及之处,需要动用国家力量开凿运河以沟通联系,缩短产粮区与消费地之间的运输里程。北京处在粮食产量普遍不高的北方,金代海陵王迁都之前已经为保障“漕运通济”把潞县提升为通州,元大都与明清北京更是极度仰仗南方产粮区的供应,建立了海运与河运相结合的漕运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下,连接南方经济重心区域与北方政治中心城市的运河系统不断完善,运河文化的内容也日益丰富起来。
国都与军事重镇是开凿运河、保障漕运的支撑点和目的地,大运河早期的历史往往与军事相关。公元前 486 年,吴王夫差为了运送北上攻打齐国的军队,命人在扬州西北修建邗城,城下开凿运河,称为“邗沟”。这是京杭大运河的开端,迄今已有 2500 年之久。东汉末年曹操为平定辽东,开凿以短程渠道沟通天然河流的平虏渠和泉州渠,北京地区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运河。曹军的运粮船得以自黄河北岸沿着漳水、清河、滹沱河向东北行进,再通过潞河、鲍丘水进抵幽州,为后来的隋唐大运河打下了初步基础。隋文帝开皇四年(584 年)开凿广通渠,由国都长安连接军事重镇潼关。隋炀帝动辄使用百万民力开渠,使后人最容易把大运河与他联系起来。隋大业元年(605 年)开凿从洛阳到清江(今江苏淮安)、长约 1000 公里的通济渠,沟通了黄河与淮河。大业四年(609 年)开凿永济渠,从洛阳经山东临清至河北涿郡(今北京西南),长度也近 1000 公里。隋大业六年(611 年)开凿江苏镇江至浙江杭州、长约 400 公里的江南运河。经过这样一番开拓,以东京洛阳为中心的河网运输系统日趋完善,东西向为主的天然河道与连接它们的运河, 大致呈现出“之”字形的分布格局,洛阳与杭州之间全长 1700 多公里的河道可以直接通行船舶。继之而起的唐朝,全面继承了隋代的运河系统。
在隋唐之前,北京及华北地区开凿的运河,如曹操、隋炀帝等人开凿的平虏渠、泉州渠、永济渠等,都是以军事扩张为目的、用以运粮运兵的水上通道,那时的运河就如同中原王朝伸向北方的一只臂膀。金元以后,南北运河的交通水利系统则成为北方政权站稳燕京、进军中原的重要依托。
辽金之后,北京逐渐成为全国首都,政治地位迅速提高,众多的人口、庞大的官僚机构及奢靡的宫廷生活,要求物资运输的规模成倍增加,每年要有数以百万石计的粮食及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华北、江南等地征收运来。北京运河的发展也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辽升燕京为南京,为加强粮食调运,临朝执政的萧太后利用永定河故道,疏浚、开挖了一条运粮河,即著名的“萧太后运粮河”。这条运河大致从辽南京城东南的迎春门南下,经今陶然亭湖一带东行,再向东南方向流经十里河、老君堂、马家湾,在通州张家湾附近接入潞河。运河两岸及河底均为黄粘土筑成,坚固无比,故民间有“铜帮铁底运粮河”的称号。萧太后运粮河首次将南北大运河和北京城直接连在一起,在北京运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金代海陵王决定迁都燕京后,为保证首都的物资供应,天德三年(1151 年) 在调集百万工匠民夫建设中都城的同时,将漕运枢纽潞县升格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大定、明昌年间,又开金口引卢沟河之水以增加运河水量,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金口河。其路线自金口引卢沟河水东出,向东南注入金中都北护城河,开渠达通州。因沿河建造闸门以节水流,又名闸河。漕船顺此, 可由通州直接驶入金中都。通州成为“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但由于卢沟河泥沙过大,金口河饱受淤积之苦,而雨季又使中都城多洪灾之虞。因此金廷后来不得不将金口堵塞,运河河道随之废弃。
进入元代后,元世祖忽必烈接受谋臣刘秉忠建议,在金中都的东北新修大都,作为南北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首都。大都每年上千万石的粮赋供应,对漕运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隋唐南北大运河的基础上,元世祖裁弯取直,先后开凿济州河、会通河,沟通了永济渠和汶水、泗水。如此,江南漕船便可由原山阳渎、淮河、会通河、永济渠,直达通州,大大缩短了南漕北运的距离。
元代也大力发展海运,南方的粮食经海道运至直沽(今天津),再经河道运至通州,最后转运大都。为了解决通州到大都之间的转运瓶颈,元朝杰出的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开凿了新的运河。他上引昌平的白浮泉水西行,循西山山麓,汇集沿线山泉,聚入瓮山泊,再经长河、高梁河引入大都城,至“海子”(今积水潭、什刹海一带)。然后出万宁桥,沿皇城东墙外南下,再转向东南与金代闸河故道相接,最后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元世祖将这条新开凿的运河,赐名为“通惠河”。从此,经河道或海道北上的南方漕船,汇集到通州之后,可进一步直接抵达大都城内的积水潭。作为漕运的终点码头, 元代积水潭一度呈现出“舳舻蔽水”的繁荣景象。运河终点物资集散、交易和人员流动推动了鼓楼西大街商业区的形成,也形成了《周礼·考工记》“前朝后市”的理想模式。鼓楼西大街是元朝大都最繁华的地方。
元代通惠河的建成,标志着三千多里长的京杭大运河全面开通,成为元明清三朝沟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持续发挥着极其重大的历史作用。明代对北京皇城及外城进行改建,北京运河随之有所变化。先是大都北部城墙南移五里,城内坝河一段成为北护城河的一部分,而通惠河的一段水道则被围于兴建的皇城之内。北京城内于是不能再通航运。通州来的漕船从此不能直接驶入城北的积水潭,只能停靠到东便门外新建的大通桥下。正统、嘉靖年间,明廷又先后抢修通州新城、张家湾城, 以卫漕运,保障天庾供应。但明清运河水源不足,成为影响北京漕运的关键。明代屡次修缮运河以维持漕运,清代又扩挖昆明湖,开凿石槽,从香山诸泉引水以济运,但问题还是越来越多。清末朝廷下令停止河运漕运,上千年的“天庾正供”宣告结束。随着现代技术的引进,20 世纪初海运的兴起和铁路的兴建,更彻底颠覆了京杭大运河作为全国南北运输主干线的地位。繁盛一时的京杭大运河迅速衰落,不少运河故道被填塞淤积,逐渐成为历史陈迹。
正是因为有了运河这条生命线,首都的稳定与国家政治职能的正常发挥, 才能获得可靠的保障,百姓形象地称之“漂来的北京城”。北京所处的地理位置偏于国家版图的东北,而有了大运河,也就有了一条强化南北联系、及时掌控江南社会动态的通道。北京作为全国首都在地理位置与经济环境方面的弱点,通过陆路通道与运河系统构成的水陆交通网得到了有效弥补,漕运与交通的发达构成了增强区域联系以及文化认同的纽带,成就了北京城作为政治中心的区位优势。
(来源:北京社科普及读物《北京历史文化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