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25-10-19
大一统与正统观念涉及在时间和空间的视野下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统治合法性的理解,它们既是中国历史哲学的重要观念,也是理解中国文明的关键概念。历史上儒者在面对不同时代问题时,通过对大一统和正统等观念的诠释,深刻地影响了王朝的政治实践和秩序建设,使得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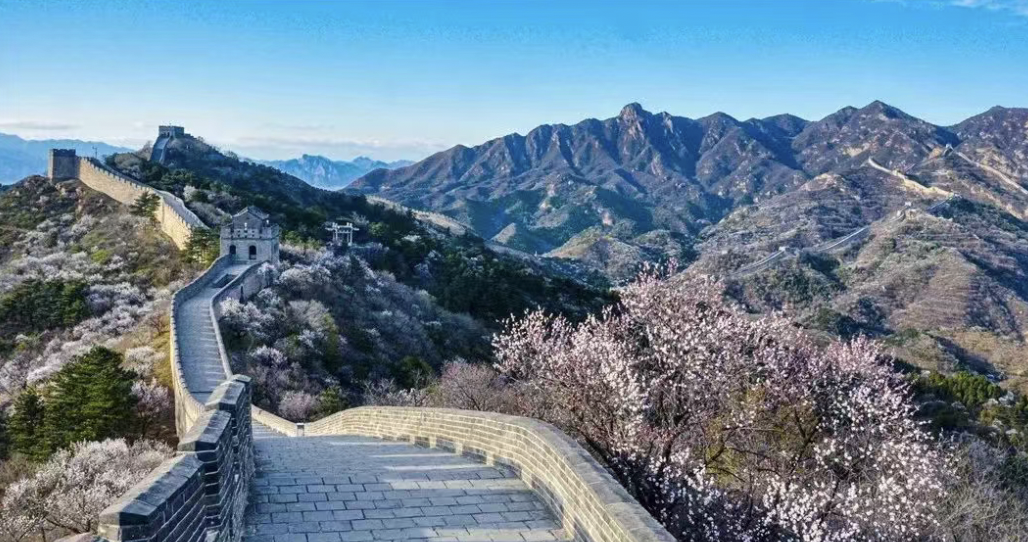
根据众多学者的解释,“大一统”的“大”,本义并不是作为形容词,用来形容地理疆域上的大范围统一以及政治上的整齐划一;而是作为动词,表示“张大”“尊崇”之意,即“以一统为大”。那么“以一统为大”是什么意思呢?
儒家文本中对于“大一统”的阐释最初来自《春秋公羊传》。《春秋》经文写到“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对此解释道:“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字面上,“大一统”是直接针对“为何强调周王之正月”的解释。生活于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指出:“周既东迁,诸侯僭擅,盖有不遵其正朔者,故称王以见鲁所秉者周礼,公羊所谓大一统,此一义也。”(《春秋稗疏》)可见,大一统的含义首先指向历法的制定,一年的时间始于正月的确定。在周天子衰微、诸侯纷争的时代,诸侯应奉行周历,张大周文王确定的历法,由历法上的统一指向对周王的尊奉。
汉代何休对经文进一步解释道:“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意思是,开端、根本具有统领总体的意义。王者受命于天,世间万物都以他为中心联系在了一起。天子通过重新确定正月初一,从而赋予万物、百姓一个人文意义上的时间开端。此时间意义上的开端彰显着天子需要担负起建构人间秩序和彰显价值的责任,建立起囊括中国与四夷的天下秩序。王者改正朔、易服色的行为表明其统治合法性来自上天以及王位具有公共性等特质。根据何休的注释,“大一统”之“统”字有着开始、开端、根本等含义。江湄教授在《正统论:中国文明的一个关键概念》一文中强调:“天下政教号令应该统一于王,于是,从时间上讲的‘大一统’义就逻辑地导出空间上讲的‘统一’义。”
总体而言,经过汉代儒者深入论述的《公羊学》大一统思想,指向了王者承接天道、从正的层面呈现一统的思路,空间上的一统依附于时间维度上秩序的安顿。可见,“大一统”的内涵包括对政治生活开端、整体秩序端正的重视,立足于天道普遍性而展开的政教生活,德化流行的天下秩序的建立,改正朔、易服色等内容。
董仲舒将“通三统”学说用来丰富大一统的内涵,强调在承认前朝合法性、对前朝制度因革损益的基础上,尊崇、张大时王的统治权威性。当三统说作为一种历史理论去解释历史现实时,统一天下的秦朝是否有资格成为其中一个统、被纳入帝王接续的历史谱系之中?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指向了作为中国历史哲学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正统论。
正统论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观念,主要涉及对继统之正与否的讨论以及如何标记历史时间等问题。正统问题的出现最初与史书编纂的编年记事有关。史家在记录历史时,需以事系年,这就涉及在现实历史的统系中,以何者为正的问题,正统地位的确定成为编年叙事的首要事务。史学家对政治统治谱系、脉络的选择,时常可以体现其对历史之正的看法及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的理解。当历史编纂不仅在于叙述历史,而且涉及确立标准以评判政权的正闰问题时,意味着史家将价值判断引入对历史现象的解释之中。对政治家来说,如何裁定前朝的正闰纷争,并阐释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是其必须面对的问题。正统问题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北宋之前,虽然人们很少用正统这个词语,却经常在五德终始框架下讨论正统问题。刘歆作《世经》以秦为闰水,强调秦朝处于闰位。东汉以来,人们一方面将具体王朝纳入德运中的一德,构建起前后相承的历史谱系,另一方面诉诸禅让、国都所在地、统治区域大小等外在条件,以论证本朝的合法性。王夫之看到了将统治合法性问题转变成政治技术操作的荒谬之处:“蜀汉正矣,已亡而统在晋。晋自篡魏,岂承汉而兴者?”(《读通鉴论》)在他看来,五德终始说没有反映天下相继的内在道理,王朝的统治合法性并不来自德运的相承。
自北宋欧阳修以来,逐渐兴起了一种不同于三统说、正闰说、德运说的正统论。主要是通过对“正”与“统”内涵的探讨,将道德原则和现实功业作为判断标准,以此来评判王朝的统治合法性。关于正统的内涵,欧阳修认为可以将其放在《春秋公羊传》的“君子大居正”及“王者大一统”中予以解释。他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欧阳修全集》卷十六)与以五德终始为核心的正统论相比,在欧阳修的论说下,正统之正从对外在因素的强调转变为统治者治理天下须符合儒家的政治伦理;正统之统从时间上的承继不断转换成空间上的一统,欧阳修直接采用“大一统”的字面意思。
欧阳修将对正统的探讨从史书编纂以及五德终始框架之下剥离出来,并试图将正统自身的问题意识予以明确,从而实现了正统论论域的巨大转变。欧阳修之后,正统之辨成为士大夫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正统论的兴盛也与人们试图重构和确认历史,探索建立在文化、族群等因素上的认同基础有关。总之,正统论背后呈现出古人对中国历史连续性、何谓中国等问题的思考,正统论成为儒家关心的重要问题。
尽管欧阳修从“居正”与“一统”两个层面诠释正统,但是其视野下的正统仍偏向于统,即当君主“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之后,该王朝仍属于正统王朝。那么正与统应该以何者为重,后世的正统论大多所争依旧在统。自正统论形成以来,史家纷繁复杂的论说、统治者的随意利用,使得正统论成为关于成王败寇的论说。在王夫之生活的时代,正统论失去了应有的指引作用。王夫之对正统观念的反思体现着其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的理解。
生活于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文明传统的存亡成为其重要关切。王夫之指出:“君天下者,道也,非势也。”(《读通鉴论》)忽视对礼乐文明延续的关注,只是将是否有一统天下的现实功业作为王朝正统与否的主要标准,不具有思想上的说服力,对权势的迁就反而会消解政治生活中的价值因素。
王夫之指出正统更应该强调“正”而非“统”,文明与野蛮是判定王朝正统与否的根据。在他看来,先王通过礼乐教化,在人伦生活的展开之中陶冶百姓的性情。立足于对民众意愿的实现、对文明的奠基,五帝三王之间形成了一个前后相承的帝王统系。三代以来,着眼于统治者对礼乐文明的保护、对政治教化的责任担当,事实上形成了承接自先王的正统王朝相传谱系,“为中国之主,嗣百王而大一统,前有所承,则后有所授。沛国之子孙若手授之陇西,陇西之子孙若手授之天水,天水之子孙若手授之盱眙。”(《噩梦》)
与汉代儒者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不同,王夫之批评了三正三统、天人感应以及承接天命而来的改正朔等内容,但王夫之对礼乐文明传统、共同体生活的关注,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的理解,与汉代的大一统学说仍有不少契合之处。
总之,对于儒家来说,君王的统治合法性并不在于现实中的成王败寇,而是来自他们对天地价值秩序的落实。当儒者将其对于价值理念的思考寄托在历史进程中的时候,呈现在儒者面前的不再是纷繁复杂的历史,而是天地之道、价值理念在历史中具体展开的过程。圣王的出现,使得价值理想与历史进程的结合成为可能,从此中国历史才有了真正的开端。这意味着王者建构起了普遍的人间秩序,人们的共同生活也成为可能。
面对先王创制的具体法度崩坏的现实,孔子通过作六经,探寻礼乐制度背后的常道,“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读通鉴论》)。对于后世儒者来说,当面对不同的时代问题时,如何立足于经典诠释,发掘自身文明的生命力,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来源:《光明日报》2025年10月18日,第11版;作者:郭征,系华侨大学生活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图片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