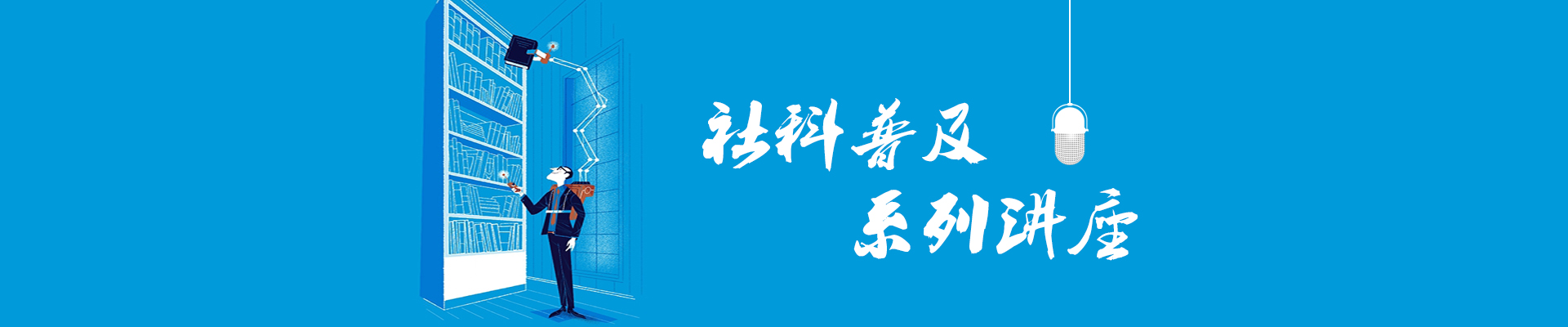来源:《学习时报》 发布时间:2025-05-28
“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是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的重要任务,是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重要方面。2025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作出了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大数据等新兴领域加强立法研究的要求。结合当前的立法实际,在加快新兴领域法律供给速度的同时,要重点关注立法的“质”与“度”。“质”主要是关注立法质量、尊重客观规律,综合运用各种立法形式,确保新兴领域立法务实管用;“度”主要是关注立法限度、厘清立法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既防范风险,也促进发展,确保新兴领域立法工作稳步有序开展。

转变立法思维,更加注重法律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当前,以互联网和数字经济为代表的领域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最快、创新最活跃、辐射最广的新兴领域,并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而不断发展变化。新兴领域很多问题在技术的加持下越来越交叉、聚焦,更加强调精准治理与协同治理,往往牵扯多个调整对象和不同法律部门,单一的部门法有时难以应对。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就是立法者从多元治理的视角,对相关问题的整体性立法设计,而难以将其简单归为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传统部门法的“特别法”。可见,新兴领域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部门法的边界,应当贯彻系统观念,充分调动各种法治资源,注重各法律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在社会变迁和科技发展中作出与时俱进的精准回应。
关注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的补充与配合。在我国,新兴技术的应用场景极其丰富,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往往有直接影响,各地普遍较为重视,新兴领域的地方立法整体呈现出活跃景象,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等。一方面,基于维护法治统一的要求,新兴领域地方立法不得违反上位法,应当与国家立法所确定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在符合法治要求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各种合理差异的存在,发挥地方立法的自主性、适应性、创新性等优势,避免对国家层面的立法规定进行简单“平移”,确保所立的法有效管用。面对当前新兴领域迅速发展对法律供给的迫切需要,通过地方立法积累相关经验是非常必要的。各地可基于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结合地方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布局、区域特点等,作出相应的具体制度安排,规定有效促进相关领域发展的具体措施。但在充分发挥地方立法作用的同时,也要避免相关地方立法“一哄而起”,产生“重复立法”问题,同时看准时机,适时整合各地方差异化、碎片化的治理规则,提炼共性规定和合理规定,为国家层面的立法积累经验。
统筹多种立法形式,兼顾“大块头”和“小快灵”。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发展的速度快,问题也产生得快,常常需要加快立法步伐,解决眼下迫切的问题。这就要求立法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化繁为简,做到急用先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研究丰富立法形式,可以搞一些‘大块头’,也要搞一些‘小快灵’”。相对于“大块头”立法而言,“小快灵”立法具有切口小、速度快和形式灵活等特征,可以采用简易立法体例,选取矛盾的一个小切口,选取急需解决的一个或几个重点问题,开展单项立法,有几条立几条,管用几条制定几条,这能够有效降低立法难度、加快立法速度、提升立法效果,较好适应新兴领域的特点。短期内,可以通过推进“小快灵”立法,对普及性高、风险较大的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进行规制,及时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加快制度供给速度。长远来看,新兴领域具有技术密集、跨界融合等特点,单项应用中往往包含多项技术,如元宇宙结合了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孪生等多种数字技术,在时机成熟时,也应推进统一的、基础性的立法,对相关基本概念和基本制度作出规定。当然,立法是一个有序的过程,按照立法法规定,不论是“大块头”还是“小快灵”,立法标准、立法程序等都是一体要求的,不能因为形式的简化而降低立法质量、突破立法程序。
加强新兴领域立法要有“度”,不仅需要知道在哪些方面应当立法,也需要知道在哪些方面不应立法、不必立法。新兴领域出现的众多议题,法律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式,也未必是最适宜的手段。例如,某些新兴领域的安全风险可以通过技术本身的优化发展或市场的自发调节获得解决,并不需要法律规制;某些新兴领域刚出现时,社会关系发展尚未成熟,技术风险的表现方式、严重程度、发生概率等皆不明确,法律制度贸然介入不仅可能错失风险防控的焦点,而且可能妨碍技术进步,甚至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有的新业态、新领域,生长得快消失得也快,仓促立法可能造成大量的立法成本浪费;等等。对上述情况,都不宜立法。新兴领域立法一定要对事件背后的立法事实进行充分发现、认定和论证,建构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估框架,深入研究新兴领域的运转机制和发展规律,研究新兴治理事项上法律、政策、道德的关系,政府、社会、市场的关系,相关主体权利、权力、义务、责任的关系,真正针对那些法律“应该管”且“管得了”的议题开展立法,坚持成熟一个、出台一个,谨防制定“无用的法律”。
确定了立法对象后,法律能够介入的程度也是有限的。新兴技术的颠覆性与快速迭代性,使得相关领域的发展与可能导致的风险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需要立法者在内容安排上粗细结合、宽严相济,在划定底线的基础上体现较强的包容度。例如,对于人工智能等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尚未定型的新业态,立法不宜规定得过细过严,而是可以由法律条文规定原则性要求,并授权主管部门制定或引用相关标准细则,将动态更新的技术标准与相对稳定的法律框架结合,避免法律频繁修订,减少企业对法律不确定性的担忧;又如,可以借鉴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等的立法经验,在严格监管的同时,推出AI沙盒和创新基金等来平衡创新,通过“硬约束+软激励”的模式,既约束行业乱象又激励技术进步。
(来源:《学习时报》2025年05月28日,第02版;作者:林珊珊;原文有微调;图片来源: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