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4-05-15
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历程与当代文学尤其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演变基本上是同步的,其获奖作品可算是当代长篇小说序列中的精品。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所评作品是首版于1985年至1988年间的作品,而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转型也在这一时期进入新的阶段。为了突破陈规,作家们对西方现代技法进行了借鉴与转化,增加了叙事的厚度与深度,而茅盾文学奖的评价标准也随着时代的新变而微调,这一时期的获奖作品在保持其审美稳定性的同时,也因新小说的加入有了持续更新、不断被阐释的活力。新小说之所以能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因为它们具有解释历史生活的能力,其基于传统文脉对叙事进行更新的经验就是值得探究的。同时,因其最接近国际潮流,也颇具中国特色,便于对外传播与交流互鉴。
讲故事传统的复归与更新
尽管受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很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都出现淡化故事情节的趋势,但要想从“小众文学”转向与无数陌生人建立联系的“大众文学”,乃至得到“茅奖”的青睐,还是要接续写实重情的讲故事传统,小说世界还应建造于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传统写实成分可以有大有小,但如果作家的描写不到位、细节不考究、逻辑不严密,小说的物质世界将因有缝隙而难以建立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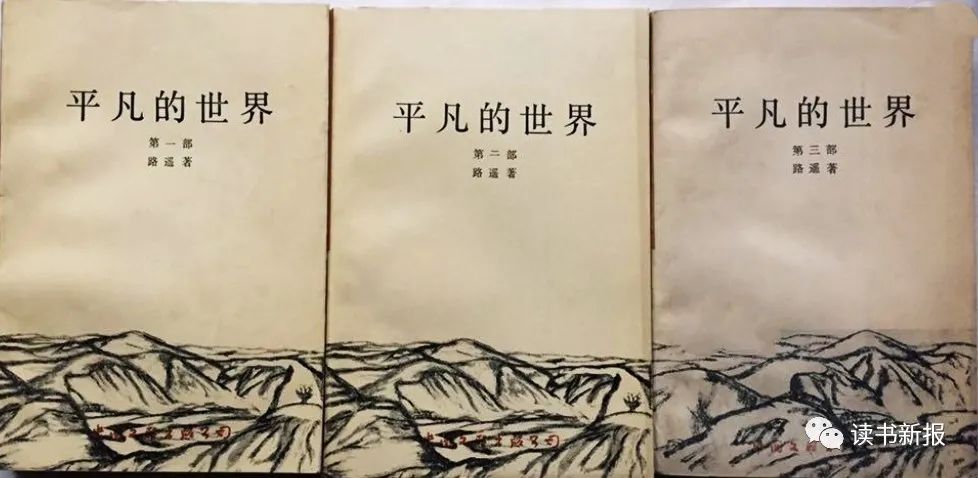
第一,讲述有深度的故事。《平凡的世界》作为第三届“茅奖”获奖作品,就是路遥从实地调研出发而写的。而他之所以选择这种实录写法与全景展示的视野,就是为了呈现一个时代的社会转型。《白鹿原》是第四届“茅奖”获奖作品,写的正是20世纪前五十年的历史。该小说以中国化的魔幻方式写出了民族灵魂的秘史。
而莫言、苏童和格非这些曾经的先锋派作家之所以能获奖,与其创作的转型密不可分。程光炜在《以历史回溯眼光看“先锋小说”》一文中提道:“增加了故事和写实元素……但那不是重视史诗性叙述结构、众多人物塑造和贯穿性大历史故事线索的经典长篇小说。”其实,他们大多回归了讲故事的传统,也尽力与饱满、及物的史诗叙事缩小差距。莫言的《蛙》探讨的是国人生育与生命延续的问题。“江南三部曲”可谓格非对百年中国历史剧变的独特观照与思索,他主要以知识分子为核心探究他们是如何改变社会,又如何消磨掉斗志以致精神蜕变的。潘凯雄在《培育中国当代文学新经典》里说道:“姑且不论莫言、苏童和格非们的获奖作品是否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品与陈忠实、路遥们笔下的现实主义不尽相同,这才是一种十分正常、十分健康的文学生态。”这说明“茅奖”评选既坚守自身的原则,同时也灵活应对时代新变,尽力使获奖作品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
第二,讲述方式的更新。贾平凹小说中的叙事得益于密实的生活细节的流动,而历史的演进、天地神灵的互动、人性的审视也充盈其中。陈思和曾提出法自然的说法,而获奖作品《秦腔》就是在法自然的生活流乃至细节流叙事中完成对意识流叙事的转化的。其中的叙述者引生相当于常人眼中的疯子,可正是他看到了传统沦落、土地荒芜、价值失序后的农村。他的内心独白正是作家的内心独白,其思绪也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徘徊。作家缅怀的正是以仁义礼智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以秦腔为代表的传统戏曲艺术、以土地为核心的传统根基。

而格非主要借鉴的是外来的迷宫叙事,在他的小说叙述中有或大或小、有时有意有时无意的疑团,同时他又在研习明清文人白话小说中更新了其叙事风貌。虽然他并未像苏童等那样快速转型,可他最终还是将西方现代小说的精巧技艺与中国古典意象融汇在了一起。而《人面桃花》里传统诗性叙事资源的渗透与转化,已经有超越外来资源的势头,诗意的叙述与意境的营造已渐渐遮住了迷宫建构的锋芒。不过在《山河入梦》与《春尽江南》中,传统诗性叙事资源已经弱化与隐形,这说明中外两类叙事资源在其小说创作中还处于不断协调中,但对原有叙事样态的更新还是颇为明显的。
饱满深切的人物形象再造
人物因小说而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小说也是因人物而立的,“茅奖”获奖作品中的人物已成为当代文学人物长廊里的重要代表。不过人物塑造不能只是某种理念的传达,不管是政治性还是哲理性,如果人物形象不够饱满与生动,即使有深度,也难免有符号化的倾向。假如写不出见心见性的人物形象,人物塑造就会流于表面化。有思想的作品在刻画时代变动时,其人物书写要切中时代的痛点或要害,且有很强的时代概括性,这样才能成为文学史上独异与典型的人物形象。
第一,有时代概括性的人物形象。《平凡的世界》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青年的奋斗历程,孙少平与无奈返乡的高加林不同,他最终进城当上了矿工,并想靠读书来改变自身的命运。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外来文化在带来新观念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原有文化,重新发掘乡土世界与传统文化的魅力成为作家创作的主题。陈忠实的《白鹿原》与贾平凹的《秦腔》都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像朱先生、白嘉轩与夏天义、夏天智等就是传统道义的坚守者、有文化积淀的智慧老者。《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如同原上的神灵一样,庇护着白鹿原。而白嘉轩的以德报怨与以正祛邪也让这部小说充满了人情之美。《秦腔》中的夏天智虽然与朱先生一样与人为善,可在这样一位长者逝去后,清风街竟没有几个精壮小伙愿意为其抬棺启墓,这与朱先生故去后众人哭灵送灵的厚葬有着鲜明的反差。而夏天义对土地的守候、夏天智对传统艺术的眷恋,都是对转型时代的经典概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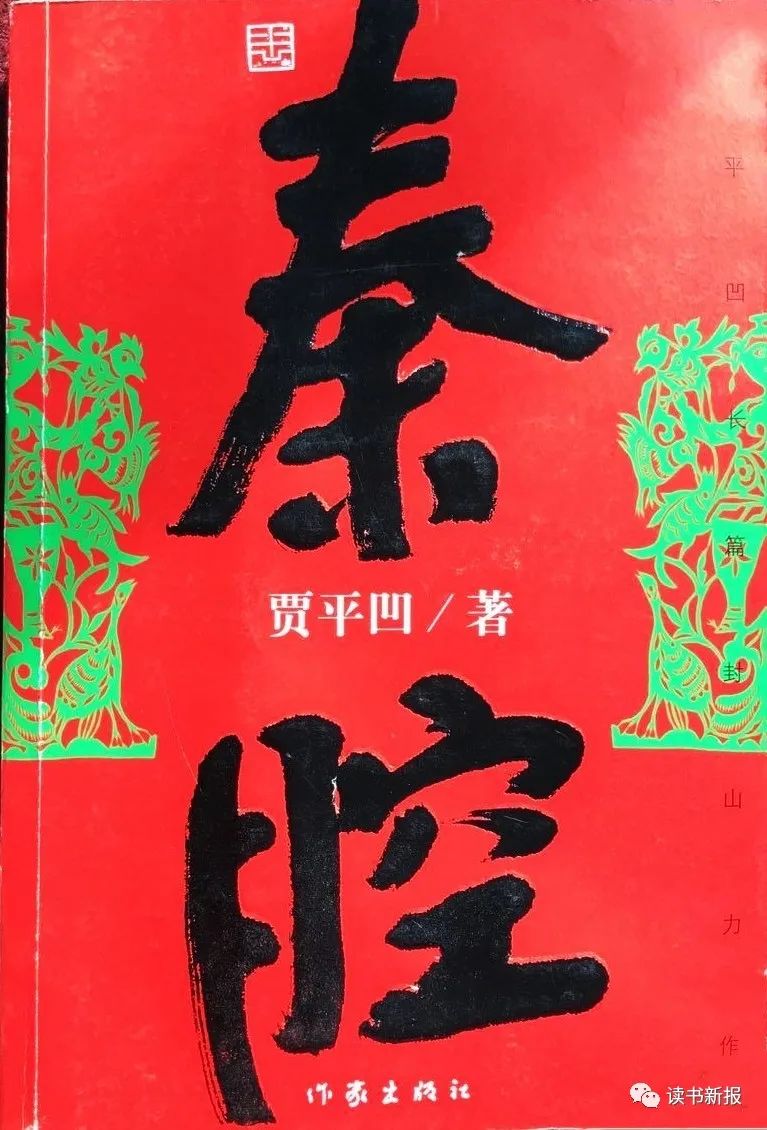
第二,对人性弱点的正视。人物形象要呈现对时代的深切把脉,这就需要作家正视人性的弱点,因此作家得是有清醒自我意识的主体。在《白鹿原》里,白嘉轩虽然没有痛苦的省思,可正因为作家的斟酌,他才被塑造成既有光环又有阴影的独特人物。在《尘埃落定》里,阿来正是借助非常态的叙述者进入历史,而在二少爷的引导下,土司内外因权欲、情欲而产生的无休止争斗得以洞见。但说到底这都属于外在介入的角度,并非源于历史人物的觉悟。因此,作家要自我审视、勘探本相,但最终还是试着协调、克服历史与现实中的难题,作家既要有人性的发现,也要有对精神的坚守,没有难度的信念可信度不高,有了人性改善的可能,对未来就更有期待。
修史立传的叙事观念
很多当代作家的小说创作不仅受到域外文学的影响,也接通了自身传统的血脉。贾平凹、莫言、阿来、格非等都在创作实践中对传统文学资源进行了有意的探寻。他们不再隐藏或遮蔽传统因子,而是通过完善阅读体系激活传统文脉,其中修史立传的写作意图与志向就颇为瞩目,所谓的先锋作家其实早已转向史诗化写作。
第一,历史总体性的再建。这一时期的获奖作品已出现从直面重大问题的大叙事向关注日常俗事的小叙事的转变。周宪在《美学及其不满》中提出:“后现代拘泥于小叙事而抛弃总体性,带来了很多严重问题,使得美学研究专注于审美现象的细枝末节,失去了对人类社会重大问题的敏感和关切。”其实,这一时期的获奖作家并没有失去对时代焦点问题的敏感与关注,而是多从个人脆弱的性情出发进行叙述,取消了整齐划一的言说模式,使历史内部充满细碎嘈杂的对话呈现出来。在此基础上,这些作品仍有对现实尤其转型期发展态势的整体把握。
因此,不管技法如何多变,获奖作家都尽力以写出所处时代的社会真实为己任,他们试图对社会发展做出全局的、本质的和符合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贾平凹就以刻画转型期的中国为自己的文学使命,其作品勾勒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动的精神地图。阿来出于对所属族群负责的态度,不断书写被边缘化的历史记忆,同时他又超越特有族群的狭窄视野,思索人类共通的存在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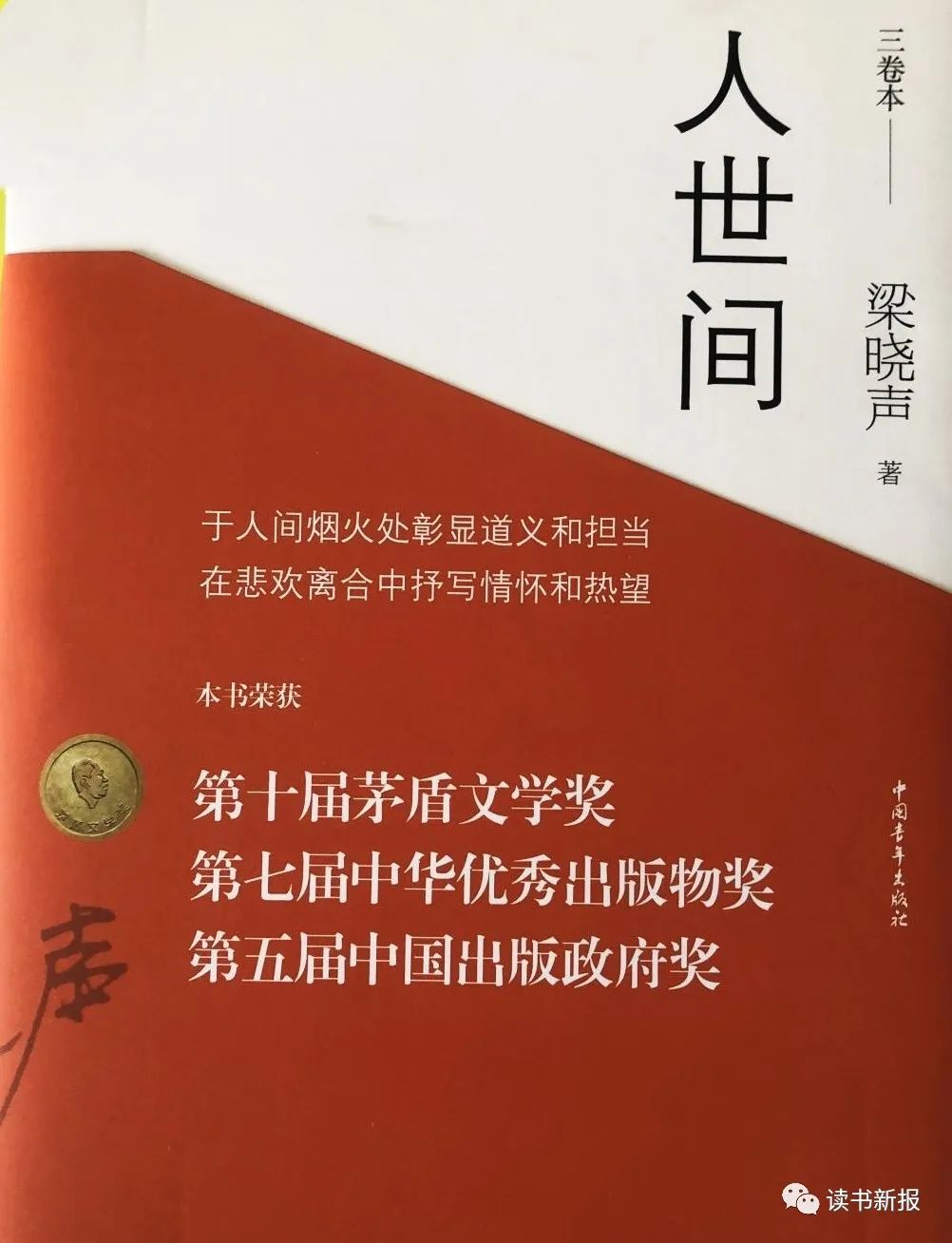
第二,从个体命运书写到民族形象建构。获奖作家直面自身所处的时代,又以不同的取向与美学反映其关注的现实。他们往往从比较熟稔的人物入手,却越来越淡化对个体命运书写而专注于对一定时代共通命运的思索。在《人世间》里,梁晓声不仅揭示出社会变革中人性的裂变,还借由周志刚与周秉义阐明其奋斗历程及作家对家国情怀的看重。而“情本体”也再现于光字片老百姓几十年的平素交往与情感关联中。周秉昆、郑娟以及共乐区工人在艰苦年代对“孝”与“义”的当代传承,都可呈现出时代演变的底色与值得弘扬的价值观。
因此,一切历史讲述都应有对当代生活的映照或启示,作家有何新的发现,所写问题与当下社会的关系如何都是颇为重要的问题。在他们的长篇小说中,可以借由人物与故事、精神与审美等,提炼出中国式的现代精神与心理结构,诸如民族心性、生存仪式、精神归宿等。这其实既是对民族想象的阐释,也能以文学的方式使中华文明深入人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5月13日,第4版;作者:樊娟,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图片来源:读书新报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