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北京老城故事》 发布时间:2023-07-03
编者按:
北京“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具有3000多年建城史和800多年建都史。这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沃土,历史积淀深厚,文化遗产丰富,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为服务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全面梳理北京老城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入挖掘和阐释北京老城的历史文化内涵,编写了《北京老城故事》一书。即日起,人文之光网摘选部分文章予以转发,敬请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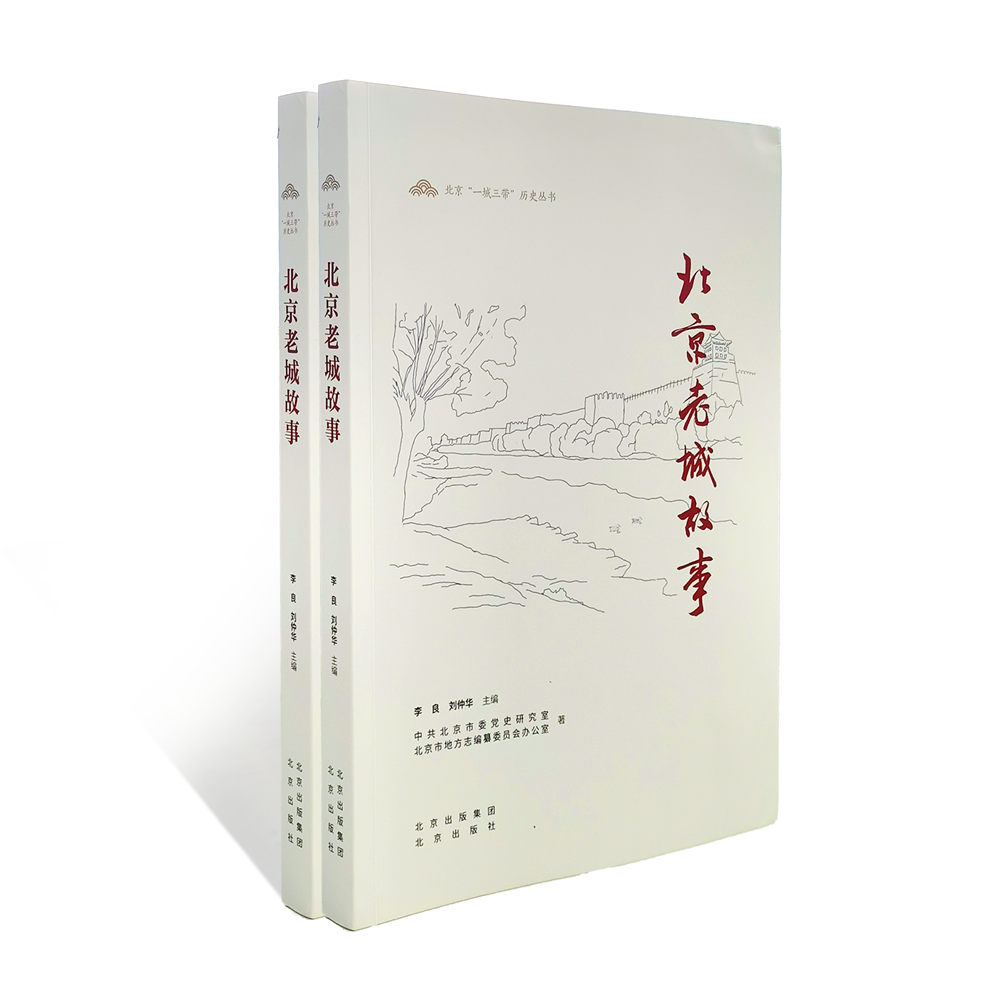
明洪武元年(1368)闰七月二十八日三更时分,夜色深沉。随着一声沉重的“吱呀”声,健德门缓缓打开,一队人马夺路而出。夜色之中,元顺帝带着后妃、太子一干人等仓皇逃往大漠……5天后,明朝大将徐达率军入城,元朝寿终正寝。
两都巡行必经之地
元朝有两座都城,其中一座叫上都,也称开平府,位于长城以北的漠南草原(今内蒙古多伦县滦河源头金莲川)。这里是元朝的龙兴之地,是连接草原与中原的纽带。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在开平集会,登上皇位。从此,开平成为大蒙古国首都。中统四年(1263),开平府更名为上都。
至元三年(1266),忽必烈令刘秉忠和张柔、张弘略父子营建大都城。9年后,一座崭新的都城拔地而起。大蒙古国改国号为元,大都成为元朝帝都。修建大都城时,在北城垣上设了两个城门,其中西面的叫健德门,取意于《易经》乾卦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元朝采用两都并立制度,健德门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两都巡幸(从大都到上都)的必经之门。元朝半数皇帝都是在上都继承皇位的。每逢漠北或辽东发生叛乱,大批军事物资北调,上都就是重要的中转站。大都夏季酷热,元朝的皇帝难以忍受,于是每年春天,都要到上都避暑;秋天一到,再从上都南下,回到大都过冬。这就是元朝独特的“两都巡幸”制度,而出入大都,都要经过健德门。
“黄金幄殿载前车,象背驼峰尽珠宝。三十六宫齐上马,太平清暑幸滦都。”元人柯九思的这首宫词,说的就是元朝皇帝赴上都时健德门前的情景。黄金幄殿,指的是皇帝乘坐的车驾,是一座两轮车,上面布置了一间由名贵木材和黄金制成的寝室,上覆精美的兽皮,点缀着许多珠宝。象就是大象,皇帝两都巡幸并非骑马,而是乘坐“象辇”。这些象有的来自云南,有的来自藩属国。出巡当天,4头驯养的大象被精心装饰一番,拉着皇帝乘坐的两轮车,后妃、太子以及大批扈从官员,浩浩荡荡地通过健德门。
留守大都的官员还要出健德门送行。等到八、九月间皇帝车驾返回时,留守官员再次出健德门,到居庸关以北远迎皇帝。来来往往,近百个春秋。就这样,南控中原、北连朔漠的元帝国,在车驾往返中被穿梭承载起来。
天怒人怨国势渐衰
健德门不仅见证了元朝鼎盛时期的繁华,也目睹了元帝国的衰败。
元顺帝即位之初,由于矛盾加剧,朝廷内耗严重,整个国家已经衰败不堪。他本来想励精图治,扭转局面,但天不遂人愿,他既没有祖先铁木真、忽必烈那样的雄才伟略,也没有木华黎、耶律楚材那样的能臣良将。当时,民间流传这样一首歌谣:“宰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
“宰相造假钞”指的是中书右丞相脱脱改革钞法,发行新钞。但是为了节约造钞成本,他就利用中统钞的背面印刷。中统钞纸质很差,存放时间又久,造假者将原有面值磨去,用墨重新描画出高面值,造成流通混乱,假币泛滥。
“贾鲁要开河”指的是贾鲁开黄河,间接引发大规模农民起义的事。大约从至正四年(1344)开始,黄河流域的水灾愈演愈烈,严重影响运河漕运。脱脱打算疏堵并举,治理黄河水患。工部尚书成遵提醒他工程浩大,花费过度,加之农民起义不断,如果起义军和河工串通,局面就会失去控制。京畿漕运使贾鲁不知天高地厚,愿意承担治河一事。结果不出成遵所料,栾城(今河北石家庄)人韩山童将刻好字的石人事先埋在河滩,当年四月下旬,黄河河工挖出独眼石人,石人背上写着“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一时间,15万河工人心思变。五月,韩山童、刘福通聚众起义,吹响了元王朝灭亡的号角。
对于这种局面,元顺帝似乎也有预感。一天,他梦见黄河千余里清澈见底,大小鱼儿历历可数,醒来后认为“黄河清,圣人生”,这是出现了要替代他的人。于是,他心灰意冷,对政事日益懈怠,沉迷声色。同时,元朝宗室内部开始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皇太子与皇后奇氏谋划,让元顺帝禅位。父子、夫妻之间为皇权斗得你死我活。
官吏贪污横行,百姓怨声载道。朝廷派宣抚使考察官吏,有人甚至编歌谣讽刺:“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
大兵压境夺门而逃
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平定南方后,决定挥师北伐,夺取元大都。徐达率领大军攻破天津,进抵通州。
匆忙间,元顺帝召集文武百官在端明殿商议,一派主张坚决守城,一派坚持弃城北上。众人激烈争吵一夜,莫衷一是。黎明时分,疲惫的元顺帝推开端明殿大门,猛抬头看见房檐上有两只白狐,双目炯炯,宛如闪电,令人胆寒。当众人簇拥过来时,元顺帝已是泪流满面。想到前些天同样出现在房檐的那只鹞鹰,元顺帝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宫禁严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朕不可复作徽钦衔璧求活,为天下笑。”他心里发誓,绝不能再像当年北宋的徽、钦二帝那样,做阶下囚,为人耻笑。
3天后的闰七月二十八日,清宁殿内,他召集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无奈地宣布:“明军已经势不可当,朕决定避兵北行。”
惊闻皇帝的这一决定,宦官伯颜不花双膝跪地,痛哭流涕:“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臣等愿率军民出城拒战,愿陛下固守京城。”
此时的元顺帝去意已决,他一面以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以庆童为中书左丞相,坚守大都,一面收拾祖宗牌位、金银细软,在夜半时分,带着一家老小惊慌失措地逃出健德门,奔应昌城(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附近)而去。
颠沛流离之际,元顺帝回想起大都城内锦衣玉食的日子,百感交集,伤感地唱道:“以诸色珍宝建造的淳朴优美的大都,……温暖美丽的我的大都……我哭也枉然,我好比遗落在营盘的红牛犊……恰在弘扬佛法之际,因昏聩而失去可爱的大都,在我的名声之下……把众民所建的玉宝大都,把临幸过冬的可爱大都,一齐失陷于汉家之众。”
歌声在空中久久回荡,马队在草丛中落寞前行,阴云低回,充满凄凉。一年后,元顺帝死于应昌城。元军残部在明军追击和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走向分裂。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700多年前的健德门早已荡然无存,新建的健德门立交桥上车水马龙,桥下的元大都土城遗址在楼群掩映、海棠花丛中若隐若现,仿佛在诉说着那段久远的历史。
(来源:《北京老城故事》,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著,北京出版社2022年版;图片来源:“北京市方志馆”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