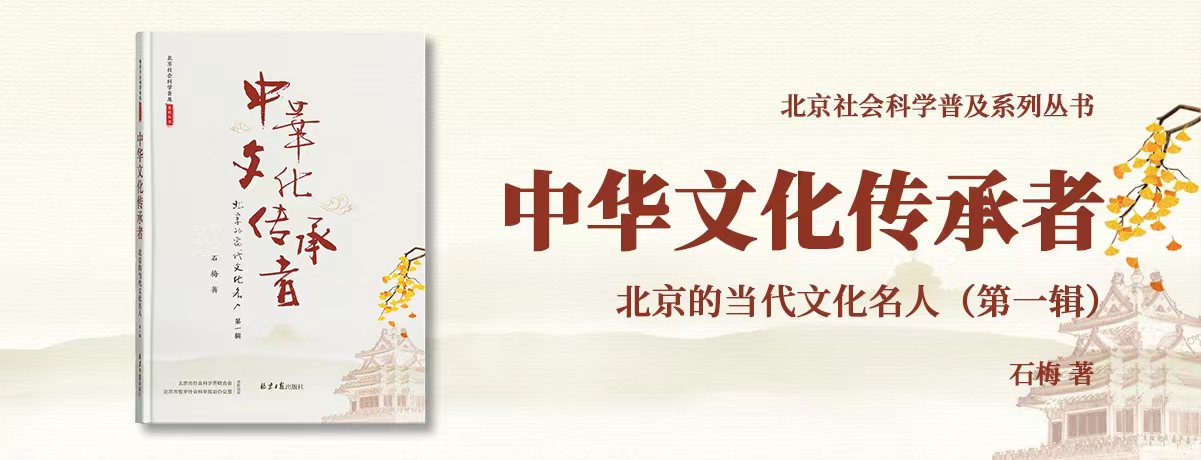来源:人文之光网 发布时间:2023-02-08
滴水虽小,却能穿石。这给我们两点启发:一为从不间断,二为注入一点。从不间断,就是有恒,日复日,年复年,坚持不懈;集中一点,就是目标专一,从不旁逸。
平静的学者,却有着不平静的经历。先生说自己:“在过去七八十年中,尝够了酸甜苦辣,经历了喜怒哀乐,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蔽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但是,不管人生道路如何曲折,这位有脊梁、有抱负的真正学者,始终都在坚持对真理不懈地追求。综观先生所走过的路,我们悟出了一个坚韧的“恒”字。
有恒,他为了一个目标,10年“洋罪”,10年灾难,却依然向着这个目标前进
因逢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德国一住就是10年。当时希特勒让德国人的腰带一紧再紧,于是,季羡林也跟着受起了“洋罪”。在飞机轰炸的隆隆声中,只能吃到配给的一点点带鱼腥味的黑面包和土豆。如果在汤碗里面偶然发现几滴油珠,也会让他兴奋地提醒同饭桌的同学。几年里他失去了饱的感觉,饱尝了饥饿的他,居然想明白了为什么在地狱里,必须要让恶人首先品尝饥饿的滋味。
但是,此时他正攻读世界上最难懂的吐火罗文。这一切丝毫没有减少他苦学的劲头。他帮房东老妈妈到山上伐树,准备过冬的木柴;一边想尽办法去弄食物,甚至下乡去帮助农民干活。同时,死啃“天书”般的语法、练习。
于是,靠着把梵文一节一节地抄在小纸条上,他居然完成了200多万字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整整8大册,足足9万行。他那时是“雪夜闭门写禁文”,自谓“此乐不减羲皇上人”。
恢复工作后,他把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他的时间以分钟计算,4时起床,上班前,为完成鸿篇巨制就已经工作了几个小时。他没有午睡的习惯,午饭后稍事休息,就继续工作。晚饭后的散步,是他活动筋骨的时候,但是,他的脑子依然也不闲着。火车上、飞机上,他也从不浪费一分钟,就是参加长而空泛的会议之时,他也会从口袋里面掏出小片纸,写着什么,那是他在构思自己的小品文章。
有恒,就是对祖国赤诚的爱,始终如一地倾注到为之奋斗的事业里
在先生回忆留学德国的文章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先生的心迹:“我的祖国母亲,我这是第一次离开她,离开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这个母亲也频频入梦。”在德国10年,他无时无刻不思念祖国。为了回到祖国,历时半年多旅程的艰辛。他搭坐别人的吉普车,绕道瑞士,在那里他写了这样一首诗:
“留学德国已十霜,归心日夜忆旧邦。无端越境入瑞士,客树回望成故乡。”
正是这发自内心的对祖国的纯情热忱,化作了他生活的动力。
问先生为什么能如此长久而毫不懈怠地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行走?先生说:“不管人类自己制造了多少麻烦,但是我对人类的前途仍然充满了信心。自渺茫的远古以来,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犹如一条铁链,一环扣一环,缺一环则链难全;犹如接力赛,一棒接一棒,缺一棒则赛不成。我们每一代人都只是铁链的一环、接力赛的一棒。我们都应该认识这种情况,努力做促进人类前进的工作,不能违反,直至全人类共同进入大同之域。我觉得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应该有这个神圣的责任感,这也是人生的意义所在。”
胸怀天下,是先生特有的人格,他就是为此而勤奋工作的。他于名利轻,于感情重。
20世纪70年代,他在离开故乡40年后回乡探亲,亲切地和乡亲们挤在一条板凳上拉家常;他经常给村子里的小学寄书,为村小学捐款,设立奖学金,鼓励村里的孩子好好学习。90年代,先生还继续为清华大学的学生讲30年代清华学子革命、爱国的传统,用一声声亲切的呼唤,告诉当今的青年莫忘前辈的光荣传统。
有恒,就是淡泊,无论花花世界多么目迷五色,他都甘于寂寞,甘于清苦
先生真正做到了“仁知双修”,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先生有无限丰富的精神世界,却甘于寂寞,过平常人的生活。正如陶渊明诗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先生身穿中山装,脚踏圆口布鞋,是极普通的长者。新入校的大学生,竟误把他当作了工友,请他帮助照管行李。对此,他也平静地照看不误。他在极其普通的状态下说话、做事、写文章。他的“三不“原则,正是他积极的人生哲学。
一不挑食:他一日三餐吃的是家常饭菜,再普通不过。绿豆小米粥,是几十年不变的佳肴。清晨,就是一杯茶、一块面包,就一点炒花生米。
他对生活要求不高,对吃喝从不计较,这与他幼时的苦难经历不无关系。先生说,那些看似绿豆芝麻般的琐事,使他终身受用不尽。
小时候,他不知道有比白面馒头还好吃的东西。因为那时平日只能吃又苦又涩的红高粱面饼子。家里连盐也买不起,母亲只能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成水,腌咸菜。
四五岁时,他就由邻居大姑、大婶带着,走出去老远,到别人收割过的地里面捡麦子和谷子。有一年夏天,他捡得比较多,母亲把麦粒磨成面粉,贴了一锅白面饼子。顽皮的他因为饭后偷拿了一块饼子,被母亲赶着打,他跳入屋子后面的水坑里,站在水中,狼吞虎咽地享用了这块饼子。
二不嘀咕:凡事他都拿得起,放得下,无畏无愁,不烦不躁,达观乐天。
三不闲着: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是,常动脑子,血液往大脑输送,可以延缓衰老。学生说他越老研究越大。他主持过几个大的学术工程,大得让人瞠目。具有如此强烈的研究、创作愿望,并身体力行,这种状态和境界,当然能最大限度激发人体内潜在的活力,从而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
从家走到图书馆,有一公里的路,他边走边想问题。他的爱好广泛,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广为涉足。他说,换一个领域,脑子就像刀磨了一样锋利。
他是“老生代“的散文大家。他的文章本色天然,极富节奏、韵律感,是他对人间疾苦、人情世态参透彻悟的曲折自然的表露。第一届国家图书奖,他首创一人获得两项巨奖的纪录。
先生有多方面的建树,是国宝级大师,却心静如水,淡泊名利。这是因为他有积极的人生哲学,他认为工作、奋斗、事业有成,于国、于民、于人类有所裨益,方为人生之大义。
20世纪80年代,新疆博物馆派专人把在新疆新出土的44张88页用婆罗米字母写成的吐火罗文A残卷,送到季老手里,他大喜过望,很快就把多年尘封的吐火罗文资料翻译了出来。季老此时在心里告慰德国恩师的在天之灵:“我没有辜负您对我的殷切希望!“
“纵浪大化”的季老,从来不喜亦不惧,总是望着新的高峰,健步行进。
(来源:北京社科普及读物《中华文化传承者》;作者:石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