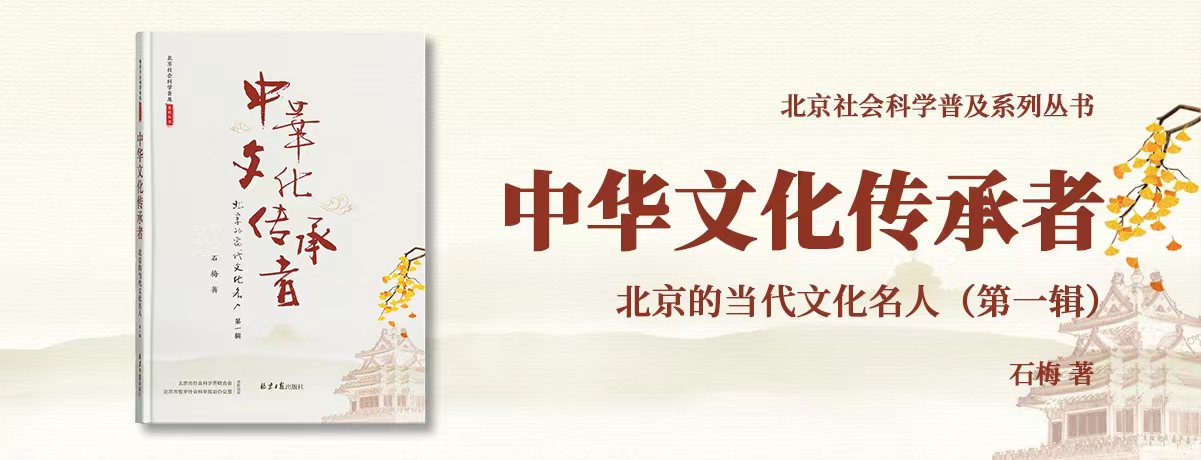来源:人文之光网 发布时间:2023-01-25
1997年的一个夏日,正当荷花盛开的时节,我来到北京大学朗润园的湖水前看荷花,在湖边散步良久。这片荷花叫“季荷”,是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季羡林亲手所植。我正在看有关季老的文字, 应《中华儿女》杂志之邀,打算采访季老,现在是为“未成曲调先有情”,我感觉写季老不能不写这荷花。

作者采访季羡林先生。
夏去秋来,秋去冬至,在一个雪花飘飘的日子里,我经过残枝败叶的荷塘,走进季老的家。刚一迈进厅门,季老的大白波斯猫就紧跟我们进了书房。季老照例坐在书桌边,我刚在他的对面坐下,猫就跳到书桌上瞪起大眼盯着我。季老亲切地抚摸了它一下,它就顺从地蹲在桌上。我看到季老的眼睛里充满了慈爱。我和季老聊了起来,我先提出的问题是他何以对学术如此追求。我注意到,这时他的眼里散发的是智慧、深邃的目光。想起有一篇报道,说季老衣着朴素,平易近人,一个开学之日,一位新生把正在散步的季老当成工友,让他帮着照看行李,他也照看不误。我想,这位学生不是没有抬头看看季老的眼睛,就是眼拙,季老的双眸明亮得出奇,就是他眯着眼睛,也照样闪动着灵光。正所谓“观书到老眼如月,得句惊人胸有珠”“气质变化, 学问深时”。
正聊着,忽然那猫一下子就跳到桌后的书柜上去了,我正想着这猫功夫够深的,只见季老站起身来,没去赶它,而是用小盘子端来猫爱吃的零食,放在地板上,还轻声“咪咪”地叫那猫。于是,那猫又乖乖地跳了下来。季老还微笑着说:“赶它,会摔着它。”无拘无束的猫吃完就排尿,于是季老又笑吟吟地拿来墩布擦干净。这种爱心“润物细无声”地打动着我。
季老与猫有着多年的交情,这猫每天清晨跟着他在北大散步,不离左右。
季老爱猫,同时与荷花也有着不解之缘。北京大学朗润园前的这池绿水,原本有过荷花,后来变得空空如也。是老人拿来洪湖的莲子, 撒在池中。一年入夏,绿水漾荡,静无信息;二年至夏,小荷微露尖尖角,在绿波中瑟瑟;三年经夏,已放数朵的荷枝,在如镜的水面上高高挺立着,举起那丰满的绿莲蓬。而后,每年春温秋肃,绿叶茂密, 莲朵繁星。季羡林经常高兴地徘徊在池边,细数着莲朵的数目,好像那满湖的碧翠,能幻化出他心中的情思。这经冬历夏的生灵,正是他人生的写照。
先生的书斋号称“书城”,共有六室,每室四壁,通天到地都是书。进入“书城”,更觉先生学问之深广;聆听先生潺潺细语,更觉先生胸襟之博大。
季老精于语言,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 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精于此种语言仅有的几位先贤之一。季老驰驱于多种学术领域,研究翻译了梵文名著及德、英等国经典著作, 诸如梵文名著《沙恭达罗》和世界瞩目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等,又是散文高手;另外,尚有诸多的各类文字,总计上干万字。而且,这些成就还是在先生香花满天的90多种职务的边角余空中取得的。望着先生的满头银发,真不知那头脑中展开着何等汗漫的宇宙, 旋转着何等浩荡的乾坤。而今,先生虽已至耄耋之年,写作尚晨昏不辍,寒暑尤工。细读先生往日的人生,才知勤奋之沧桑。
啃高粱饼子度过童年,上中学时竟喜欢上了蝌蚪文似的英语,20世纪30年代同时考取最高学府清华和北大
正如哲人所言:艰难能造就伟大的心灵。季羡林家境贫寒,是属于中国的最下层,他于1911年8月出生在山东省临清市的官庄,父辈生活无着,童年充饥的是红高粱面饼子,就熬盐碱土水腌的咸菜。
但孩子自有孩子的乐趣,大苇坑中捉青蛙,草丛里找鸭蛋,树枝上摇知了。跟着大人捡一夏天麦穗,最后可得到母亲做两三次白馍的奖赏。他最大的兴趣是看“闲书”,和小伙伴们一起学习书中的侠客武功。没有学好武功,却养成了倔强的性格。有一次,在小学校里, 因带头反对老师体罚,反而被老师打得手掌肿得老高。
靠着叔父的接济,季羡林在济南读完了小学上了中学。
有一件事情,使他钓虾捉蛤蟆的兴趣发生转变。他当时就读的高中附设于山东大学,校长是有名的书法家、前清状元王寿彭。季羡林 15岁时,因得到一次全校甲等第一名,得到了状元公亲书的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的表彰。季老说这对他的影响万分巨大,使他从此勤奋读书,想如果下学期不考甲等第一,那这张脸往哪儿搁呀!这时,他才觉得自己即使不是一条大龙,也决不是一条平庸的小蛇。
还有,他竟然喜欢上了英语。那蝌蚪文一样的文字,竟然能发出奇妙的声音。于是,他沉迷于神秘的曲线声音中,进而,喜欢上了外国文学。他节衣缩食,每年大约能省出两三块大洋,就用这钱去买英文书。当从邮局取回寄来的书时,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然而内心里却增添了极大的力量,一种用语言文字所无法表达的幸福之感油然溢满心中。为取书走了 20多里路,却一点也不感到疲倦,回来的路上他觉得天更蓝,水更绿,连鸟鸣也更加悦耳。
以后,他和80多个高中同学,北上京城投考大学。结果,只有 3人高中,而他同时考取北大和清华,他选取了清华。凭着他的执着, 拍打着激浪,跳跃过了这个龙门。从此,这个穷孩子,徜徉于知识的海洋中。
1930年初入清华大学,大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满眼是书的高山,满耳是诗的乐章。
他听郑振铎教授讲课,如闻高山流水,滔滔而下。在先贤的引导下,他笔下生花,写出了很多文章,还到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做编辑。
有一次,他听了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又引发起对梵文的兴趣(他说陈教授的这门课和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令他受用终身)。当时,他朦胧地知道,中国文化与印度的梵文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在这朦胧的意识里,他接近了这个世人都感到朦胧的梵文的迷宫。越是迷宫,越引起他浓厚的兴趣。
“昨夜西风凋碧树”之时,他望尽“天涯路”,此时他发现了自己的道路。我们感叹学者的作用,一代学者启迪了下一代学者,环环相扣,使学术的生命无穷尽地延续着。
在当时的清华大学,有四位学习佼佼的学生被称为“四剑客”, 他们是李长之、林庚、吴组缃和季羡林。
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应济南母校的邀请,季羡林回济南中学任国文教员。这时,他有了妻子、儿女,有了一个虽清贫但温馨的家。
不久,清华与德国互换研究生,清华选中季羡林留学德国。这真是一件好事,却又要与家人远别。但是,家人表示,再苦也要让他去, 以光耀门楣。
1935年8月1日这天,叔叔、婶母、妻子德华、女儿婉如及尚在襁褓之中的儿子都送他出了家门。在亲人的眼泪中,他登上了汽车。那眼前逝去的破屋,屋顶的残砖败瓦,瓦上的枯草,和着他的眼泪, 进入了他永久的记忆中。
辘辘的车轮声,裹着他的离情,向着寒冷的北方驰去,又驶向更寒冷的欧洲,踏入了遥远的德国。
在“二战”的轰炸声中,在难忍的饥饿中,咽着带腥味的黑面包。德国面壁10年,取回“真经”,精通了已经作古的梵文和吐火罗文
游子最突出的感觉就是思乡。原本是两年的学业,不期,由于世界的动荡,把他的归途阻断,在德国一住就是10年。
他来到小城哥廷根,一到那里,马上就被眼前的美丽和洁净感动了:绿草铺就的大地,辉映着浩荡的蓝天,即使是冬日,白雪下依旧是绿草碧翠。面对如此美景,他想的依然是故乡夜空下苇坑里的小月亮,常常是梦到母亲,哭着醒来。
最初到德国,面临的是学业的选择。学什么?来之前,在中国, 一个相识的朋友劝他学“保险”,说为将来的生计,这是铁饭碗。但是,这与季羡林的情趣大相径庭。他倾心于中国文化,而且原来朦胧的想学梵文的念头在这里逐渐清晰了。
他知道要把中国的思想史、文学史搞清楚,不研究印度的东西, 不懂梵文是很困难的。而梵文研究最具权威的当时就是德国,这里有世界著名的梵文学者。季老说德国人有一个特点,也可算是民族性,离他们越远的东西,他们越感兴趣。于是,他投在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门下。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对教学非常严肃认真,尽管选读梵文的学生只有一个,而且还是中国人;但是,他还是正正经经地上课,一丝不苟。
学习是艰苦的,梵文是世界上最难懂的文字,更何况流传下来的是残缺不全的贝叶,更何况老师教法的特别。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讲课,第一、二堂课念一念字母,第三堂课起就读练习,天书一般的梵文,语法就只有靠自己课下准备,常常一节课要准备一天。
季羡林既然已经决定,则知难而进,每日苦读不已,居然日有所获。在很短的时间里,进入了这艰难的门径。
此时,“二战”开始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应征入伍,换了一个 年届古稀的西克教授。西克教授的绝活儿是研究吐火罗文。
吐火罗文分A、B两种方言,后者又称“龟兹文”,学的是新疆出土的文献,这种文字是古代流行在吐鲁番一带的语言。它比天书一般的梵文还要难懂,世界上能读懂它的只有西克教授等一两个人。西克教授不容商量地把这种稀缺的残卷影印本摆在了季羡林的面前, 大概因为季羡林是中国人。于是,季羡林又每日沉浸在这迷茫的语言中了。
语言虽然近于迷茫,而目标是明确的。逐渐地,他和西克教授的感情越来越亲近,下课之后送老师回家,搀扶着西克教授,一师一徒, 一老一少,行走在冬日的夜幕中,踏着厚厚的白雪吱吱作响。其景其情,为季羡林所永远不忘。
博士论文终于写完了,论文答辩的日子已经确定。季羡林心里有些慌。这心慌本来是正常的,任何学生在考试前心里都在成与不成中徘徊。但是,季羡林还有一个原因:他初到德国,见到很多留学生,而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国内达官贵人家的纨绔子弟或者衙内。他们留学不过是换了一个玩耍的地方,整天花天酒地,反正有的是钱,不在乎取不取得博士文凭。然而季羡林却很在乎这文凭,因为如果得不到文凭,回国以后就与那些纨绔子弟成了同类,并且危及饭碗。他下决心要拿到博士文凭,一吐胸中之闷气。
论文通过了,成绩是“优”,而且引起了一个小小的轰动,被教授赞不绝口,说“论文有了突破的意义”。季羡林心满意足地认为没有丢中国人的脸,可以无负于祖国和亲人了。
但是,紧接着“二战”的炸弹袭来了,德国法西斯残忍地把德国人民也推入了灾难的深渊。美、英、法的飞机,把炸弹下雨般地倾泻到了德国的大街小巷。一幢幢大楼坍塌了,季羡林也如同池鱼般地和德国人民一起东躲西藏。
更严重的是食物的缺乏,让原本悠哉游哉的德国人陷入了饥饿的泥沼。季羡林整日饥肠辘辘,面包没有了,黄油没有了,连德国人酷爱的咖啡也没有了。咖啡豆贵胜黄金。当时的一幅漫画,画的是一枚高贵的戒指,上面镶嵌的不是珍珠,不是宝石,而是一粒咖啡豆。
为了找食物,季羡林想尽办法。有一次,他找到了一个为乡村农民摘苹果的机会,报酬是几斤土豆。他大喜过望,急忙赶回家,一下子就把五六斤土豆都煮了,一下子全都吃了,可是,肚子竟然毫无饱的感觉。
又有一次,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了点面粉、黄油和鸡蛋,急忙到糕点店特制了一个蛋糕。望着这块贵如黄金的蛋糕,尽管自己忍不住咽口水,但还是把它捧到了老师西克教授的面前。
西克教授一看,激动得双手颤抖,接过蛋糕连“谢谢”也忘了, 就高声地喊他的太太。季羡林看到教授如此激动,自己也感到莫大的安慰。师生之情,其浓若是。
师生情谊本该如此,季羡林更为感动的是:教授们视科学如生命。
有一次,大轰炸刚过,季羡林急忙赶去看西克教授。路上,他看到一个老人正弯腰曲背在观察着什么。走近一看,是德国飞机制造之父、流体力学权威P教授。原来,他正在观察一段短墙是如何被炸弹的气流摧毁的。他赶到西克教授家里,教授家的玻璃都被炸成了碎渣,而教授还伏在满是碎渣的桌子上,依然聚精会神地看他的吐火罗文。 季羡林真的看呆了,他感叹教授们是如何忠于自己所献身的科学。
那时,哥根廷大学有一个汉学研究所,所内有比梵文大许多倍的汉文图书馆。十几万本汉籍,他本本感兴趣。他每个礼拜都要来这里几次,读书到了 “死啃”地步,空荡荡的六七间大房子里只有他一人。
他盘桓于成排的大书架之间,看书架上摆的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 心里充满自豪感。
10年后,季羡林要回国和房东告别时,无依无靠的德国房东老妈妈号啕大哭;但是,季羡林必须要离开她,去找那生他养他的祖国母亲了。树叶经10年的飘摇,渴望着落在家乡的泥土上。他感慨地说:“山川信美非吾土,飘泊天涯胡不归。”
“不可接触者”翻译出了世界瞩目的印度史诗;坐拥“书城”,预言“21世纪将是东方的世纪,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将再领风骚”
苦难到了尽头,但是混乱中回国谈何容易。四处打听,得知只能取道瑞士。于是,和几位同命运的留学生,于1945年10月坐着吉普车,颠颠簸簸地进入瑞士。在瑞士,等候签证数月,方才冲破阻力,乘火车,入法国,登轮船,滞西贡,过香港;终于在1946年5月,经半年多的时间,才踏上了阔别10年的故土。
回来了,他的梵文研究也停止了。季羡林在德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精通了世界上极少数人才能读懂的吐火罗文、吠陀语,以及梵文等。 他的关于印度语言的论文发表,受到世界梵文学界的瞩目。他致力于印度史、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1946年,赴北京大学任教。
新中国成立了,1951年,他作为中印关系学者,参加了访问印度文化代表团。
后来,他把妻儿和婶母接到了北京(母亲已去世)。但是,其乐尚未品尝出滋味,又一个10年的“风雨”,使得他的家门窗破损,周身寒冷。
“文化大革命”来了,这场灾难尽人皆知。但是,事物总是“阴阳合璧”。游街、批斗、挂牌、住牛棚,季羡林都一一“品尝” 了; 最令他悲哀的,是他被宣布为“不可接触的人”。生在人世,不能与任何人交谈,好像独步于荒漠。他被分配掏大粪、看门房、守电话,,发信件……
大雪纷飞,他独自望着楼前落尽叶子的白杨,想到荷花也蜷缩在淤泥中,做着春天的梦。自己不也处在严寒中吗?但他坚信,池塘里的荷花,会重新冒出淡绿色的大叶子;春天,会回到大地。
于是,他把原来没有时间细看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罗摩的故事在印度是一个悲剧,主要是宣传道德伦常和一夫一妻制)搬入了自己的脑海里,沉入了诗的意境中。在看门、收发信件时,思考着翻译的韵脚。走路、吃饭,精力都集中于此,一节节地抄在小纸条上,一字字、一行行地翻译。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此非妄言。终于,在“无人接触”的时间里,他翻译出了以后使他享誉海外的《罗摩衍那》。这是汉语的首译本,8大册,9万行,历时整整10年,为中印文化交流大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那质朴的大脑里依旧白云舒卷,不知老之将至。他不觉得老,乐于做各种事,哪怕被数不清的会议催促,他也不觉得烦,高高兴兴地如约而至。
1995年的一天,在家里写作,开会的时间将到,待开门之时才知被家人锁在屋里。怕惊动别人,已84岁的他,索性推开窗户从1.7 米高的阳台上跳了出去。不料,跌坏了脚,他依然一瘸一拐地走去参加会议。另人问起,他反倒乐呵呵地说:
“跌了一下,脚虽然受伤,但检验出了五脏还结实,也是好事。”
他最大的爱好是读书,抓紧自己的每一秒钟。凌晨4时,天空还 布满繁星,他已伏案读书,开始工作了。他喜欢同时做几件事情,他的6个房间,分类贮藏书籍。在这个房间写佛学文章,累了,就到那个房间写散文(面对荷塘)……他把这称为“散步”,交替而行。每天, 头脑中智慧的思想似清泉喷涌,从他的笔下泻到纸上。他的思想,就如飞升的大鹏,在阔海上翱翔。
先生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断言:21世纪将是东方的世纪,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将再领风骚。
王阳明曰:“夫道必体而后见。”先生悟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犹如一条铁链,一环扣一环。而先生正具备东方式的顿悟、洞察力和圆融之智;又在西方文化中汲取了严谨、理性、逻辑与分析。他正身体力行,分秒必争地把他的研究成果系统地整理出来,进而开拓更宽阔的研究领域,以推动祖国文化的发展、东方文化的繁荣。
先生倡议组织全国研究东方文化的力量,撰写《东方文化集成》, 亲任主编,计划用10年的时间,撰写出版500种书,涵盖东方各国文化。这个浩大的跨世纪文化工程,于1995年启动。当时,先生于坐八望九之年,使命感还如此强烈,精神还如此旺健,真可谓老而弥坚。
先生是智者,是文化道德的传播者、实践者。他生活淡泊,有一个“三不”原则:不挑食、不嘀咕、不闲着。名誉地位于他视如浮云。他特别喜欢陶渊明的这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他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清淡平和的人格,半个世纪中,教化了多少北大及全国的莘莘学子。
先生是仁者,宽厚、爱人又重亲情。自己过着俭朴的生活,却在北大设立了 “季羡林奖学金”。他多次给家乡的小学校寄书捐款,甚至还托人给儿时一起在苇坑里戏水的小伙伴,捎钱买衣服。几十年的世间沧桑,恍如隔世,儿时的小伙伴得到这份心意,感动得老泪纵横。
先生脚踏一双圆口布鞋,身穿一身普通的中山装,头上却仿佛已经升华出一束自然的灵光,那是先生心中宇宙“天人合一“的辉煌。
季老手植的荷花,蓊蓊郁郁[ wěng wěng yù yù ]地满布池塘,荷花艳艳,莲叶田田。那莲花中端坐着的绿莲蓬,依然如佛尊般地望着季老,不知季老头脑中的宇宙,还要吹拂着什么惠风。
(来源:北京社科普及读物《中华文化传承者》;作者:石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