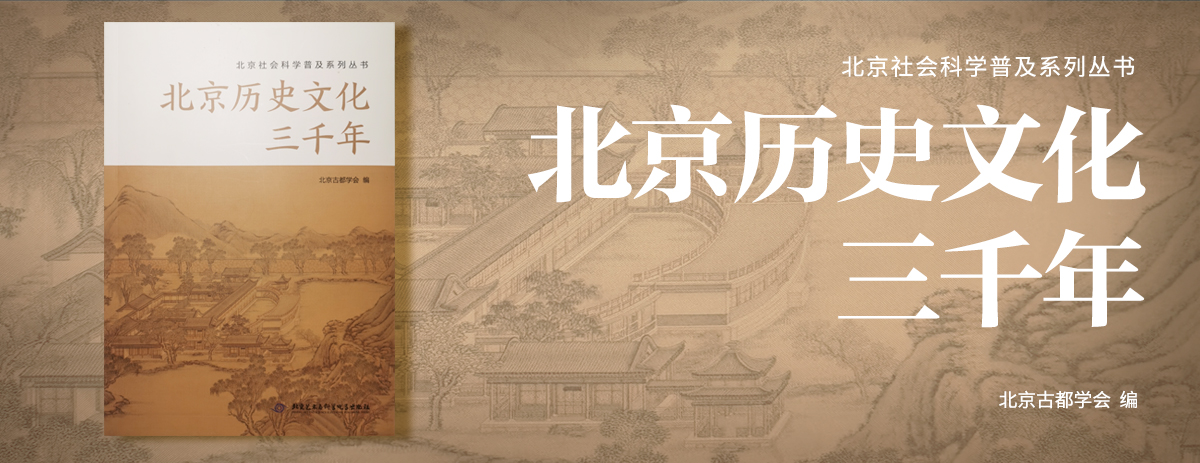来源:人文之光网 发布时间:2021-06-18
北京都城文化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较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的燕文化,进而发展演变为汉唐时期的幽燕文化,然后才逐步走向金元明清时期的都城文化发展序列。从宏观的视野来看,我们可以把北京的文化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北京没有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之前,这时的北京文化,只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流派;第二个阶段,是在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之后,这时的北京文化,逐渐变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派别。如果对北京文化进行更为细致的阶段划分的话,先秦时期的燕文化可以作为北京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也是北京地域文化的形成阶段,其突出的文化特点,是表现出北方民众粗犷、侠义的民风民俗。秦汉至隋唐时期是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全国出现了从较长时间的大一统局面转变为分裂割据局面,再回归到大一统局面的情况。而北京地区主要处于中央统一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军事对抗的边缘地带,使得其文化表现出了边塞战争的突出特色。
相对于有着广阔腹地的中原文化,燕蓟之地长期被视为苦寒之地,民风粗粝、彪悍,“燕赵多有慷慨悲歌之事”,燕国太子丹好养侠客,赵惠文王好养剑客,崇尚侠义精神,传统儒家文化与礼仪在此地影响不大。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所进行的改革,也对原燕国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一时期的幽州文化不仅包含原燕地丰富的地方文化,而且经过文字统一及思想控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燕地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不过,在秦王朝的文化政策下,战国时代流派各异的学术大都潜归民间,而能大行其道的只有秦始皇最为醉心的方术文化了。燕国方士卢生就是其中活跃的一员。
汉继秦之后进一步构建大一统社会秩序和郡县制为主的郡国并行体制,这样,先秦的燕文化之国文化在表面上似乎有所抬头,但主流仍遵循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体制下的地域文化。随着汉武帝设立“十三州刺史”政治制度,幽燕文化得以正式确立。
西汉初在幽州文化中曾占主导的是方术以及黄老之说,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在幽州传播开来。虽说汉代学术文化的中心自然在政治中心的都城,但幽州地区也不乏经学传播,燕地的文化也开始兴旺起来,如诗学传播者韩婴就是燕地学术文化的代表。东汉时期,出现了范阳卢植、涿郡崔氏等海内大儒,使得幽州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影响也较为广泛深远。
在汉末动荡后经历三国时期的调整,政局与经济渐渐趋于稳定,魏晋时期幽州经济有所恢复,文化因此再度得到发展。自袁绍与曹操争夺河北时,大量河北士人就归于其帐下,河北士人地位的提升对幽州士人也不无影响,从而带动了幽州文化的恢复。
魏晋定都邺城,邺都的文化较为发达,由于地理位置上的邻近,文化中心的辐射力也启动了幽州的文化发展。自西晋以来,少数民族移徙幽州络绎不绝,十六国北朝时期更是大量內迁与汉族杂居,形成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局面。这一时期幽州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汉文化被少数民族上层所接受,得到前所未有的传播;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习俗也给汉文化社会带来诸多影响,胡汉融合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以及社会风气中都有鲜明体现。北朝末期,胡汉融合的社会文化渐渐趋向定型。胡汉交融的局面,为幽州社会带来新的风尚,少数民族崇尚武功的习气,给幽州历来重儒学礼教的文化氛围增添了勇武的气息;语言、音乐以及服饰等生活用品与习俗都渗入到汉人社会,丰富了幽州的文化色彩。
隋唐时期,在大一统政治环境下,幽燕文化融汇多民族的特色,变得丰富多彩。从隋代以来,幽州逐渐成为东北军事重镇,大量入驻的军队以及不时发生的战争,给这里添加了金戈铁马的壮烈之风。从军的官吏与边塞诗人亲临其境,创作了大量边塞诗文,吹起一股边塞文化的热潮。与此同时,大量少数民族移民迁入幽州,其民族文化逐渐渲染了幽州民俗风情,胡族风俗逐渐融入幽州社会,胡汉融合的社会文化已经成为幽州文化基调。尤其是唐朝后期,特别是藩镇割据时期,幽州地处东北边塞,在周围割据藩镇以及边塞少数民族包围下,减弱了与中原发达文化区的文化联系与交流,文化发展局限于本地及周边的交流,因此地域特色文化更加突显。
文化的孕育、形成,离不开所处的地缘环境。燕蓟地区正处于北边区、海滨区以及三晋文化区域的交接处,于是成为具有不同区域文化风格的过渡带。幽燕文化孕育了丰富的精神内涵,其中礼贤下士的黄金台精神、慷慨悲歌的侠义精神、以勇力著称的尚武精神、多民族融合的民族精神等,都是历史留给后人的珍贵思想文化遗产。
燕昭王为振兴燕国,采纳郭隗建议,遂为其建造一座崇台,置千金,用以招贤纳才,人称“黄金台”。由于金台招贤,使得燕国由弱变强,并一举大败强大的齐国,荣列战国七雄之一,“金台招贤”被后世传为人才史话。自战国之后,在北京地区曾有10处以黄金台或金台命名,多数是慕名而生,但从另一层面反映了“黄金台”文化的影响和传播。文人墨客发思古幽情,题写了许多以此为主题的名篇。如清康熙皇帝曾写过一首《黄金台怀古》的诗:“昭王礼贤士,筑馆黄金台。矫矫昌国君,奋袂起尘埃。市骏固有术,贵在先龙媒。但得一士贤,可以收群才。”黄金台是否真的存在,它又在哪里,这些似乎并不重要,它已经被抽象为一种文化、一种尊重人才的精神。
关于幽燕民风,史书说其“雕捍少虑”“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桑”,这缘于“地边胡,数被寇”的地缘与历史环境。燕太子丹养勇士而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形成了燕地任侠尚勇的世风。愚悍少虑,这是其不足;敢于急人,这是其长处,也就是后世所谓的慷慨悲歌。唐代著名诗人韩愈曾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宋人黄裳也有“燕国多悲歌感慨之士,余风犹有存者”的感叹。虽然“感慨”二字远离战国以来燕文化的精神内涵,但至少反映出汉唐以来文人学士对燕丹遗风的关注和传播。
多民族的融合是幽燕文化的突出特征,这在北京都城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亦是关键性因素,民族融合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包容精神,同样是北京历史上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从秦时起一直到唐朝末年,每当汉族统治者势力强大,内足以镇压农民起义,外足以扩张势力、开疆拓土的时候,就一定要以蓟城为经略东北的基地;反之,每当汉族统治者势力衰微,农民起义作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而日趋激烈的时候,东北的游牧部族,也常常趁机内侵,于是蓟城又成为汉族统治者的军事防守重镇。经过汉魏隋唐的发展,幽燕文化表现出了自身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内涵,为北京成为北方乃至全国政治与文化中心奠定了基础。
(来源:北京社科普及读物《 北京历史文化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