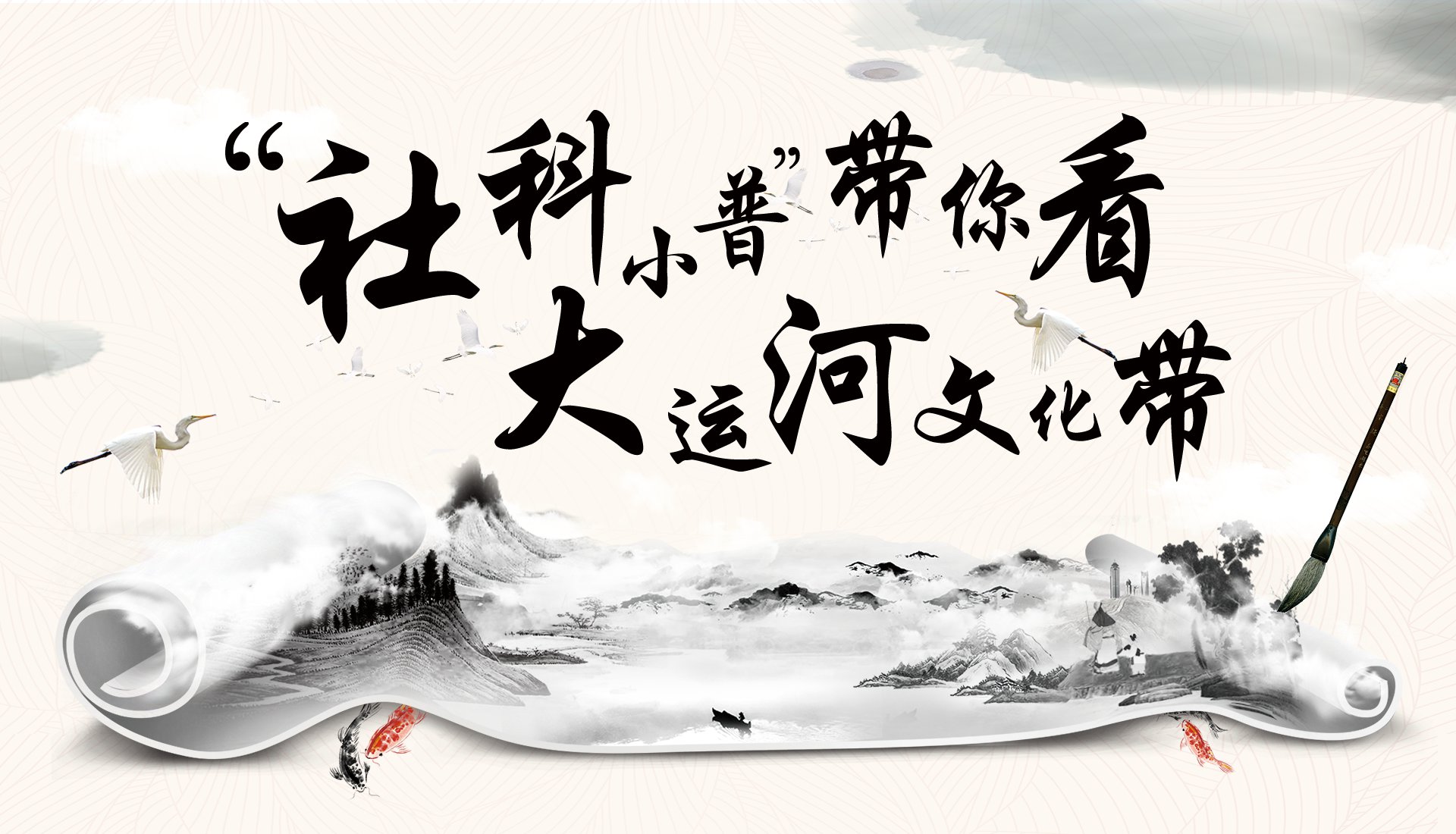来源:《南方周末》 发布时间:2015-12-01

就像人说“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一样,“批林批孔”之后,我再也不会批儒批孔。
如果出现大规模流血,最后一定是个比较独裁的人出来收拾残局,克伦威尔、拿破仑还算好的,更坏的还有。
能否从“君主下的贤贤”走向“民主下的贤贤”,即在民主制度的大前提下实行某种贤人政治。
近日,两个事件引人关注,一是薄熙来案开审,二是薛蛮子卷入性交易漩涡。法律与道德,于官于民,各自的标准与分际如何,需要澄清。放在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转型大背景里,从传统礼治到当今法治,道德与法律各自的功能,更需要厘清。多数人都希望建立一个“好社会”,但什么是好社会?建立好社会的基础和路径是什么?建立现代中国,除了要落实宪法,还需要探讨宪法所植根的道德原则。公民们除了在法律之下生活,还需要理解法律与道德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一句话,转型中国亟需清晰且被普遍认同的大纲大常。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何怀宏的《新纲常》一书,副题便是“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前些日,在何教授满壁是书的客厅里,南方周末记者请他分享了他对这些“纲常”的思考。
道德纲常是维系社会方舟的巨缆
南方周末:
现代人普遍接受的是“权利话语”。很多人认为,纲常名教是贬义词,跟专制、压抑等联系在一起。比如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等。为什么用纲常作为思考的中心?
何怀宏:
这里确实有“百年误解”,动辄说“礼教杀人”,而没理解到纲常也可能是维系社会方舟的巨缆。社会需要一些非常底线的原则或“基石”。比如,在传统社会,有尊尊、亲亲、贤贤的原则,有生命原则、保民爱民的原则等。能践行这些原则,就会治,否则就会乱。在当今的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领域,我们也需要确立一些基本的道德原则。这些原则与传统的三纲有很多区别,但也有不变的内容。例如,不一定从儒学中能直接推理和引申出来民主,但完全可以相容。旧纲常可以调整到新纲常,有常有变。常,比如生命至上;变,比如平等。而且,常更根本。
南方周末:
这些新的基本道德原则是什么?
何怀宏:
其一,民为政纲,重新定义国民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治理者要对民众负责,且这种问责不仅是民生的,还应是民主的。
其二,义为人纲,即把人当人看,把不可杀害、不可盗窃、不可欺诈、不可性侵等原则规范作为所有人的基本义务原则。
其三,生为物纲,即努力保障所有物种的共生共存。
此外,还可以从关系着眼,处理好天人、族群、群己、人我、亲友之间的关系等等。
南方周末:
把“生为物纲”列为新三纲之一,是否提得太高了?
何怀宏:
我看过诸如复活节岛的例子,最早是波里尼西亚人发现那个岛,像天堂一样,过了几百年,没有一棵树、没有鸟了,为什么?生态破坏了。这也是一个灾难,如果是说整个地球都像这样一个状况,那也要完蛋。这是世界的问题,必须提到基本道德原则的水平。
南方周末:
生为物纲意味着把物恰如其分地当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竭尽全力地榨取自然。但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
何怀宏:
是挺难,有些人比较绝望。平等是现代人追求的,但它和保护生态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大矛盾。平等的社会意味着什么?所有价值观都是允许的、合理的,但大多数人的追求往往偏物质,艺术家、科学家、政治领袖是少数。过去托洛茨基设想,新的社会,每个人都能达到歌德、但丁、达·芬奇的水平,但这不可能。在一个平等社会,各国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多数老百姓还是最关心经济。
物欲膨胀的结果就是破坏生态。多少算够?过去青山绿水靠什么保证?物质生活水平低。儒家讲节欲,道家更明显,机器最好不用,会有机心。但平等社会不一样,看起来多元,其实也可能很一元,即大家都奔物质。
南方周末:
民为政纲指向民主政治。蒋庆提出,王道政治要有超验的、历史文化的、人民同意的三重合法性,从可操作性来说,似乎是一个乌托邦,而且跟现代社会个体主义式的自主性与政治趋势有背离。你怎么看?
何怀宏:
这也是有意义的构想,是有某种现实意义的乌托邦,看起来实现不了,但反映了天人之间和人性之中的某种真实。确实,民众的意见需要得到充分表达,但少数精英的理性、对天或某种超越性的尊重也很重要。当然,我觉得要考虑现代社会的可能性和次序性,但不会去批判这些思考。就像人说“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一样,“批林批孔”之后,我再也不会批儒批孔。
今天谈道德纲常还有用吗
南方周末:
吴思先生认为叫“纲常”是一种引起关注的话语策略?他认为转型过程中利害计算毫无疑问是第一位的,道德良知只具备次要作用。
何怀宏:
这个我不太同意,我觉得在利之外,还有义,有天经地义。生死抉择时的说谎可以理解和原谅,但不意味着说谎就是对的。简单用利害计算来说是不妥的。
我相信有一些在所有人心里存在或潜存的天经地义,比如不可杀人、不可伤害无辜。即便不受惩罚,杀人也不容易,正常人一般情况下杀不下手。为什么刽子手这一合法职业不管怎样有一种不洁的东西在,使人们避之唯恐不及?
但人们也会疯狂,尤其在一种集体暴力中,甚至有变成英雄的许诺。社会最需防范的就是这个。而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诉诸人们心中对天经地义的道德直觉。
南方周末:
小月月被碾压,也有人视而不见,能说他们有这个道德直觉吗?
何怀宏:
我想还是有的,但是被埋在心里了,他自己不一定意识到。具体的行为会被现场气氛引导,小女孩倒在那里了,开始几个人不管,后来都不想管了。但后来很多当事人说,自己以后再碰到这样的事一定会做点什么,打个电话也行。
南方周末:
良知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来培养出来的?
何怀宏:
我觉得本来都有的,但很容易放失。比如利益的诱惑;比如别人强暴了我,要报复;或者是权位很重,可以像隐身人一样,干坏事受不到惩罚……这就会丢失本然良知。孟子说的恻隐之心是一个道德动力的根基。
南方周末:
为什么个人安排自己的生活有道德性?基督教文明里是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现代社会有天赋人权的说法作为依据。我们对此是认同即可,还是需要提出更有力的根据?社会纲常是否需要精神信仰的支持?
何怀宏:
吴思也提过这么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仅仅中国的问题,而是整个现代世界的问题。在传统社会有一种信仰、敬畏,现代世界整个“脱魅”了。反宗教和无神论把神甚至“天”都弄掉了。但你也可能无法,也不应当再重新依靠政治权力来“神道设教”。在信仰问题、价值问题上不能强求一律,不能说没有的人一定要有,这要从心里生发出来,不是权力规定,但你至少不要去破坏宗教,破坏信仰的植被。对信仰要尊重,哪怕不理解都要尊重。我们要感谢中国的少数民族,是他们给我们更多地保留了一些信仰,哪怕是“原始”的信仰。少数民族聚集地一般比汉人聚集地的生态好,他不轻易破坏自然生态。作为教徒也都可能不那么太功利、太物质,太世俗。
南方周末:
台湾社会转型后也面临这种困境,但他们的佛教等发挥了一些调节作用。
何怀宏:
是的,所以需要一些非功利的、精神的调节。但追求精神的人比较受冷落。知识人去争取一个自由社会、平等社会,实际上追求的是一个自己将被冷落的社会,但至少不会受到残酷的猎杀、莫名失踪。这一点是为自己争取的。但是,会有市场的压力、物欲的压力,你会比较另类。所以要有思想准备。即便这样,为什么还要去争取?因为让个人安排自己的生活,本身就有道德性,即使不赞同别人甚至多数人,道德上还是要尊重别人的选择。你可以倡导,但不能用权力强制别人。
南方周末:
怎么理解个人也存在争议。比如社群主义对原子式的自由主义就有一些批评。张祥龙先生提倡儒家特区,认为民主、法治的形态应该有中国的特点,比如家庭的价值。
何怀宏:
中国太需要各种自愿社团、民间社会。只要能够自由进入和退出,就应该鼓励。应该鼓励各种实验。有人说,要重新恢复人民公社,可以啊,以色列也有公社,但是要可以自愿进入和退出。现在组织的训练显得更紧迫重要。走向民主,必须通过一定的权利和义务的训练,以养成现代政治文明需要的人格和行事、思维习惯。
政治责任与生命第一
南方周末:
伦理领域总是很难有革命性变化,但政治领域的变化要大很多。
何怀宏:
政治领域不一样。君为臣纲,表面上打破了,但20世纪我们经历了比过去君主统治更厉害的全权统治。过去海瑞骂皇帝这类事,即便当事人被处死,其他老百姓、官员是同情他的,但现代全权社会里,在上面发起的群众运动中,你会众叛亲离。
“父为子纲”有亲情保证,绝大多数父母对儿女有亲情,会关照儿女的利益。政治领域不一样,我们应该强调民为政纲。
古中国不像古希腊,那么多政制可供选择,儒家只看到君主制,只能改良君主制。现在有了选择,不能避而不试。个人来说,过去可做隐士,现在不可能了。
南方周末:
这涉及个人权利与责任的问题。论语里有句话“乱邦不居”,如果各方面环境很糟糕,即便是儒家也认为可以移民?
何怀宏:
不是所有人都能移民,也有成本问题。有可为的情况下,绝大部分会选择留下,如果觉得已无可为,已经“鱼烂”,大乱已经发生,能走的就走了。
现在的知识分子也不像上世纪上半叶及其之前的士大夫型知识分子了,责任感不会那么强烈,因为不像梁漱溟他们有种“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责任意识,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已变成平等的,甚至边缘的阶层,地位不是特别重。过去全国就几万文官,责任特别重,乃至到民国时期知识分子都非常爱国,责任感很强,都想回来报效祖国。后来打成“臭老九”,你要求他尽那么高的责任,责权不符。
南方周末:
多数知识分子还是主张渐进地改良,这跟生命原则相关?
何怀宏:
我在《新纲常》一书里说,如果出现大规模流血,最后一定是个比较独裁的人出来收拾残局,克伦威尔、拿破仑还算好的,更坏的还有。个别人认为只要乱就好,好像乱到一定程度会自然出现一个新世界。但这有很大危险。
南方周末:
即便是战场上,也要做到“跟我上”,而不是“给我上”。自己可以去流血,但不可以自己躲在后面,却去号召别人。
何怀宏:
就是自己流血也号召别人流血,都还有危险。要把生命原则放在第一位,使社会不崩溃。
所以我把法治放在民主之前。实现民主途径要有法律的统治,通过法治训练、公民训练到民主选举。在实行民主选举之后也还是始终落实法治的,不走这样一条路,就可能会是走向暴力冲突的劣质民主。
南方周末:
基于生命原则,你应该也赞成在法律上废除死刑?
何怀宏:
赞成。但可能是逐步废除,我也不知道最后能到哪一步。有些残杀孩子的,我会犹豫,太匪夷所思了。但要有生命至上的信念,我们有其他惩罚手段,可以把他关一辈子。当一个人生命受到直接威胁时,可以杀死对方保护自己。但你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已经把他抓住了,可以把他关住不为非作歹了,是否一定要杀死他?这是一条线,哪怕对一个快要死的人,主动去杀死他,也不行。用老子的话说,“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者矣”。基督教也认为上帝是“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有些东西是人不能越俎代庖的。人为地去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总是有某种凶险和恐惧。
南方周末:
也反对安乐死?
何怀宏:
这是他自己的意愿。如果一个人留了遗嘱,家人也同意,我不会特别反对,也可能不会特别支持和倡导。有的人很痛苦,生不如死,觉得活着太没有尊严,每天处在痛苦之中。但即便这样,也不是积极地去帮助他死,是消极的,不是打针促进死,可能是放弃治疗等等。主动安乐死需要更强有力的理由。
市场经济、物欲与道德
南方周末:
市场经济和社会道德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何怀宏:
市场经济本身有一种道德性,让个人自主安排自己的生活、消费,尊重人的主体性。计划经济是认为有些人比另外很多人高明,资源集中也可能造成腐败、浪费。
但哪怕再健全的市场经济,在价值上,它以物质效益为中心导向。手段上,是竞争,虽然比武力或权力配置好多了,不过还是容易出现问题,容易用各种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严格的法治,比较困难,法治也是一种强制。我承认市场经济有道德性,但不认为道德应以市场经济为基础。
南方周末:
反过来说“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基础”似乎也不全合适,法治更有效。但法治又需要道德根基?
何怀宏:
坑蒙拐骗肯定不行,市场经济必须有某种强制约束,价值上受伦理引导。一是要有人道底线,包括保护市场经济中的弱者、失败者。二是不顾一切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不行的,地球也将承载不了。人还有其他需求。欧洲真正成熟的市场经济,可说是不那么锱铢必较的市场经济,很多人一辈子就做小店主,发展不到麦当劳、肯德基那样的连锁店,做不到那么大,但能够维持自己体面的生活,周末2天度假。这样反而比较健全,不是一门心思竞争,还有钱买不到的东西:情感、友谊、兴趣等。
南方周末:
健全的生活需要在个体层面的平衡,市场经济可以提供这样的空间。似乎不矛盾?
何怀宏:
要有平衡,不走极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确实都要力求中道,避免生态灾难、政治灾难、战争灾难。尤其中国处在一个转型期,很可能出现一些预料不到的情况。
“平等”难题与贤能政治
南方周末:
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都给我们带来了平等。但平等也会带来社会向下滚的危险?
何怀宏:
对。现在我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平等和物欲的冲突困境,也许人类面临很大的灾难后,不是要求实行民主,而是要求某种权威。比如在很大的生态危机,城市出现大洪水之后,可能要约束某些自由和财产权。一部分人财产全部失去了,还有一部分人的财产全部保留了,生命优先,紧急避难,哪怕是你的庄园,别人就要在这里住,要吃你庄稼地里的东西,要不然活不了。整个人类社会遇到这样的灾难,可能就要约束一些权利。那时治理不一定是大家投票,而可能是权威治理,危机时不能政出多门。
南方周末:
但也不意味着是独裁政体,那也蕴含着极大的危险。
何怀宏:
用西塞罗的话说,可能还是某种混合政体比较妥当。斯巴达有两个国王,有元老院、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最有权力,有时元老院掌握更多权力。古罗马也实行过,有不同的比例和比重,没有很单纯的政体,都是某种程度的混合政体,但以什么为主却可能要因时因地制宜。
南方周末:
怎么看待贤能政治?
何怀宏:
我曾经研究现代选举与中国古代察举和科举的异同。考虑过能否从“君主下的贤贤”走向“民主下的贤贤”,即在民主制度的大前提下实行某种贤人政治。选举官员可以设置一些门槛。美国也有年龄限制,总统必须多少岁以上,必须成熟一点,过去有财产限制,这或许不应该,但有财产的人更有责任也不是全无道理。古代还有文化资格限制,你必须读四书五经这些“道德文章”,读得滚瓜烂熟,久而久之会受一些精神浸染,才能进入官场。诗文也要达到一定水平。古代官员字都写得好,拿到现在都是一个著名书法家。现代社会可不可以有类似的门槛?当然,今天文化素质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政治素养,这是政治家的首要品质。对法律的尊重、对社会和基本道德的尊重等等。
南方周末:
新加坡比较偏向贤能政治?会把社会上最优秀的一些人发展入党,赋予权力,让其担负政治责任。
何怀宏:
新加坡的精英政治比较明显,一党独大很多年,它也允许某种自由。现在的政治稍微有一些松动,反对党的力量在增加,哪一天可能也会走到轮流执政。这个社会稳定,但毕竟是一个小城邦,好控制。但比较异类、有创造性的艺术家、思想家很少,可能本来就很少,因为地方太小,也可能出走了,有些憋闷。台湾地区就大一点。
南方周末:
怎么理解以前所说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何怀宏:
现在最重要的是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多大权力的官员,不能逾越法律,不受惩罚,不管多卑微的人,被侵犯、被伤害了,不能求告无门。
在过去的等级社会里,老百姓的道德主要是风俗,不需要政治上的礼仪,他不参政。等级社会要考虑名分问题,跟老百姓不太一样。老百姓犯法了到衙门去,可能当庭褪裤子打屁股,如果是秀才,他有个名分,一般就不这么羞辱他,需要保持某种名分的尊严,在当时,也有一定道理。但现在不一样,不可能依靠这种距离感、神秘感来维护秩序。
道德与法律的边界
南方周末:
前段时间“常回家看看”入法,是否是法律侵入道德领域?
何怀宏:
要求子女常回家看看,如果放进刑法肯定不行,但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里提到也可以。但即便如此,落实这个条文还是很难靠权力执行和惩罚,而主要是靠舆论、良知,靠劝导。如果盲信法律,可能还激化矛盾。
一个进步的社会,应该越来越多的行为被划为私域,而不是划入政治领域。一个全权主义社会可能把几乎所有行为都纳入政治领域,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把很多行为纳入自己约束,或某些自愿的组织去协调,而不是权力干预。
南方周末:
私德不好的人,怎么在公共领域评价他?比如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曾被政府监控到参与性交易等等。比如管仲,个人生活奢侈,但对社会秩序、国家治理有贡献。
何怀宏:
要区分对人和对事的评价。只要是正当钱财,我们虽然不赞赏奢侈,但也无从谴责或惩罚。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谈盯紧坏事,慎说坏人。对坏事恶行要有正义感,但涉及对整个人的评价要慎重。老说别人是恶棍、人渣,这样的人往往自己就成问题。一个人即使做很多坏事,只要他活着,还是可能翻盘。而有些好人,也突然做出坏事。对一个人的评价甚至盖棺还不能论定,但好事就是好事,坏事就是坏事,涉及行为的道德标准还是应当比较明确。
南方周末:
最近薛蛮子被警方以性交易为由行政拘留。李银河一直主张性交易非罪化,怎么看待这样的主张?
何怀宏:
这应当主要还是属于道德领域而非法律领域的事情,但有两点需要考虑:一是是否有公权力介入其中,如果是公开或隐性的“权性交易”,法律是应该管的;二是社会的观感,如果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感觉因此被冒犯了,大概也还是会有程度不同的法律的约束。有一些人性的弱点,我们不能说这不是弱点,但也无法完全消灭这些弱点。
要特别注重手段的正当
南方周末:
有人说,转型过程中,好制度才会生长出道德,之前主要靠利害计算,君子才能追求好的德行。儒家也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怎么看这种区分?
何怀宏:
面面俱到的完善君子很难,普通人就可以有基本的正义感、同情心。社会氛围很重要,要有意识地往善加点砝码,天平就向善摆过去,有人率先做,就会有跟进,不要求所有人都成为君子。说古代社会是君子社会,也不是说大多数是君子,或要求大家都成为君子,只是尽量把少数君子选拔到社会上层,起示范作用,你要比老百姓做得好,对你要求高。和传统社会等级制相应的是一种“上严下宽”的道德等级制。
南方周末:
这是法律还是道德的要求?
何怀宏:
制度和德性有重合的一面,或者说对制度可以从道德的角度去评价。就像市场体现平等自主的德性,法治也体现平等对待的正义。有些义务既是道德义务,又是法律义务,尤其是在接近底线的层次。
南方周末:
最近南方周末报道唐慧案,引起很多争议。追求公正的过程中,是否可以用一些不太合适的手段?
何怀宏:
作为求告无门的弱者,可能会这样做。她的遭遇非常令人同情,但追求任何正义的目标,手段也要力求正当和干净。重要的是其他人,比如说媒体和知识分子应该有支持也有鉴别。对媒体而言,归根结底,呈现事实是基本的要求,虽然你可以考虑在什么时候呈现才不会伤害到太弱的弱者。总之,要支持正义的诉求,但不能不讲究手段。否则目标会被手段异化,最后转到反面,这是20世纪中国最惨痛的教训。